中國工程院院士郝吉明:環境污染防治成產業升級、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推手
時間:2021-06-29
來源: 每日經濟新聞
作者:李可愚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在黨的領導下,我國生態環境保護事業取得前所未有的發展和進步。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確立了“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對生態文明建設作出頂層設計和總體部署,將綠色發展作為“十三五”乃至更長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理念,生態文明建設全面發力,不斷深入,取得積極進展,揭開嶄新的一頁。
我國的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經歷了怎樣的歷程?我們是如何改善空氣質量等關鍵環境問題的?展望未來,中國的生態環境保護將在碳達峰、碳中和背景下迎來哪些新機遇?
近日,《每日經濟新聞(博客,微博)》記者(以下簡稱NBD)就上述問題,對我國著名生態環境領域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郝吉明進行了專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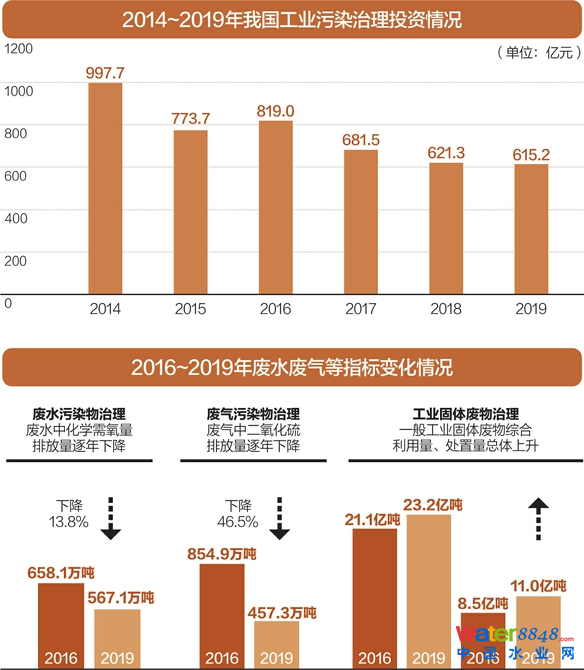
污染防治促產業升級
NBD:我國環境保護事業是如何從無到有、不斷發展起來的?在這一過程中,有哪些標志性事件?
郝吉明:回顧歷史,中國環境保護事業的一個重要開端,應該是1972年斯德哥爾摩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當時,中國派代表團參加了這次會議。1973年,中國召開了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確定了環境保護32字工作方針,即“全面規劃、合理布局、綜合利用、化害為利、依靠群眾、大家動手、保護環境、造福人民”。
1983年,我們召開了第二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這次會議的一個標志性成果是將環境保護確立為基本國策。這極大地增強了全民的環境意識,并把環境意識升華為國策意識。在這樣的背景下,制定各項環境保護政策、健全環境保護的法律體系、加強環境保護的科學研究、發展環境保護的高等教育都開始向前推進。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也面臨著如何正確解決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之間關系的問題。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過程中擺正環境保護的位置很重要。
長期以來,我們單位GDP的能耗比較高,到了本世紀初,鋼鐵、水泥、有色金屬等產量在全世界占了很高的比重,煤炭消耗占比也達到全球的50%以上。與此同時,我們的環保產業起步比較晚,科技力量明顯不足,生態環境壓力也越來越大。
再往后,中國決定再次申辦奧運會,如何保障奧運期間的空氣質量不僅僅是一個環境問題。因此,我們差不多花了十年的時間研究北京的空氣質量保障,大家意識到中國的環境問題決不可能依靠簡單的一兩項措施得到解決。
在這樣的背景下,黨和國家采取了一系列舉措:一是推動高耗能高污染行業污染物減排,走新型工業化道路,以環境優化經濟;二是修改中國的環境空氣質量標準,并陸續修訂各個行業的污染物排放標準。
黨的十八大站在歷史和全局的戰略高度,對推進新時代“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作了全面部署。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五個方面,制定了新時代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戰略目標。
2013年5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進行第六次集體學習,我就“大力推動生態文明建設”作了重點講解。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發表了講話。他強調,建設生態文明,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黨的十八大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明確提出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這標志著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認識的進一步深化,表明了我們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堅定意志和堅強決心。
在這樣的背景下,《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發布,也就是“大氣十條”,隨后又發布了“水十條”“土十條”。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環境污染成為必須攻克的現實難題。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堅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的攻堅戰,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得到人民認可、經得起歷史檢驗。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定位也就更加明確了。
2018年,國務院印發《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明確提出大力調整優化產業結構、能源結構、運輸結構和用地結構。這是源頭治理之策,從過去的“末端治理”為主改為全過程控制,標本兼治,同時提出大氣污染物與溫室氣體協同減排。
我們過去偏重強調總量減排,現在要以環境質量為核心,帶動空氣質量改善;過去重視局地性污染,但研究發現對于復合型大氣污染控制,必須推動區域聯防聯控。
抓產業結構、能源結構、運輸結構和用地結構的調整,我們抓住了關鍵,抓住了問題的癥結。所以環境污染防治成了產業升級、高質量發展的一個重要推手,而不是經濟發展的包袱。我們的環境質量也有了較大的改善。
打好藍天保衛戰
NBD: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生態環境事業取得不俗成績,其中,大氣質量明顯改善是百姓普遍點贊的關鍵進展。這些年來,我們是如何打好藍天保衛戰的?在大氣治理技術上,我們又取得了哪些突破?
郝吉明:在大氣污染防治方面,我們首先解決了酸雨的形成和治理問題。從本質上來說,酸雨的出現是酸性物質的沉降強度超過環境承載能力,導致水體和土壤酸化。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減少酸性物質的排放量,對于中國來說,主要就是減少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考慮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差異,我們還劃定了酸雨和二氧化硫控制區,首先在污染最突出的地方解決酸雨污染。經過近三十年的努力,我們基本解決了酸雨污染問題。
第二個方面的進步體現在燃煤發電廠的污染物控制上。電力行業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必須堅持高效清潔。“高效”體現在發一度電耗多少克標準煤,“清潔”可用發一度電排放多少污染物表征。
國家多次修改燃煤電廠的污染物排放標準。目前我們的標準已經是國際上最嚴格的標準。從“七五”開始,國家就把燃煤電廠的污染物控制技術研究列入科研計劃,做到了技術先行和技術引領。同時,還出臺相應的經濟政策,主要是對達到超低排放的電廠給額外補助,這樣一來,企業的積極性就上來了。
有技術支撐,有政策引導,我們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效清潔燃煤發電體系,解決了對電力的需求,也基本解決了由此引起的環境污染。
第三個巨大進展就是機動車污染控制。我從1993年開始研究這個問題,因為意識到隨著社會的發展,汽車進入家庭是早晚的事,要早做準備。
上世紀90年代中期,北京市主要走“舊車改造”路線。實踐表明效果并不好。最經濟可行的方法還是要加嚴新車的排放標準。經過20多年的努力,我國現在的排放標準已經從“國一”發展到了“國六”。同時,油品質量也實現了與國際接軌,建立了與之相匹配的交通管理體系,做到“車、油、路”一體化控制。現在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汽車生產和消費國,機動車導致的環境污染控制也取得較大進展。
第四方面進展就是我國的產業正在朝著環境友好型轉變。煤炭清潔高效燃燒、鋼鐵多污染物超低排放控制等多項關鍵技術推廣應用,促進了空氣質量改善。繼燃煤電廠實現超低排放之后,隨著鋼鐵、建材、有色冶金和石油化工等行業逐步實現超低排放,我們的環境質量會越來越好。
實體經濟是中國經濟的主要支撐,所以解決環境問題不能主要依靠壓縮實體經濟規模的方式實現,重點在于實體經濟需要實現環境友好,通過對主要行業的升級改造,用高質量發展的方法來保證產能。
我國應盡早實現碳達峰
NBD:在碳達峰、碳中和背景下,我國的生態環境未來將在哪些方面著重發力?如何把降能降耗和生態環境保護更好地結合起來?
郝吉明:“十四五”時期,我們提出以碳為核心,減污降碳協同增效,抓住了當前生態環境領域的核心問題。通過推進碳達峰、碳中和,不僅可以促進美麗中國目標的實現,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也會彰顯我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
相對來說,碳達峰是第一步,是比較容易實現的,但關鍵是什么時候達峰,“峰”又有多高?如果達峰時間拖得很晚,這個“峰”又很高,會給后面的碳中和增加很多壓力,所以我們應該盡早達峰。同時,這個“峰”應該是一個相對低的“峰”。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要把碳達峰、碳中和納入總體布局。我們只要把碳的問題抓住了,環境質量的改善特別是大氣環境的改善就有了根本性保障。
NBD:今后一段時間,哪些技術的推廣運用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實現“雙碳”目標?
郝吉明:我認為,首先還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強化節能措施。中國單位GDP能耗目前還是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果我們能夠提高能效,把單位GDP能耗降到世界平均水平,就能節約6~8噸煤,可見減排二氧化碳潛力之大。
同時,我們還要讓未來十年成為清潔能源大規模發展的十年。我們實現碳達峰、碳中和,關鍵還是要靠清潔能源。國際能源署最近發布的報告指出,未來10年太陽能(000591,股吧)和風能要迅速擴張:2030年之前,太陽能光伏每年新增裝機630吉瓦,風電每年新增裝機390吉瓦,增速達到2020年紀錄水平的4倍。交通運輸方面,電動汽車的銷量也要大幅度提高,到2030年,電動車在全球汽車銷售中的占比將由目前的5%提高到60%以上。
到2030年后,我們要大力推動建筑節能改造、交通運輸節能改造、工業節能改造。同時,也要給綠色氫能創造機會,把可再生能源轉換為氫能,解決風光發電的儲存。隨著光伏發電等技術效率的提高,光轉化為氫能的效率也會更高。
當然,未來還會有一定比例的化石能源,這就需要發展碳捕集技術,目前這個技術的成本比較高,還要解決碳儲存的穩定性問題。但現在我們必須有所準備,使其成為實現碳中和的最后一個“殺手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