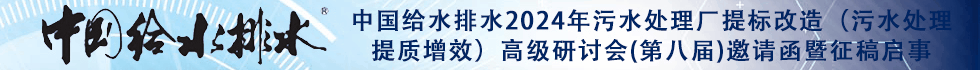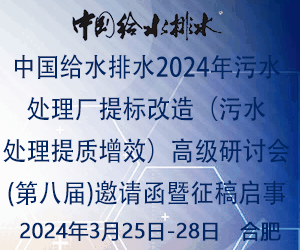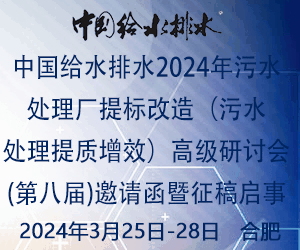蘭州水污染事故進一步發酵,從目前官方的通報中,不難得出一個事實,造成這次污染的污染源早已存在,而且相關部門和企業對污染源的存在是知情的。那么,這個27年前埋下的隱患,為什么到現在仍未根除?
此次自來水污染雖發現的“偶然”,但污染源卻早就存在,且相關部門知情
在14日召開新聞發布會上,甘肅蘭州威立雅水務集團稱:3月8日,該廠已進行了水質檢測,下次的檢測應是9月8日。4月之所以能檢測出苯超標,是因該廠承擔了上級布置的任務,此次檢測出苯超標純屬偶然,屬正常工作之外。而考慮到一般情況下中國自來水廠的日檢、月檢所覆蓋的指標十分有限,威立雅的此次聲明無疑是句“大實話”。
相較于威立雅的聲明,更值得深究的是13日晚間來自官方的消息。當時官方明確了,含油污水的成因是原蘭化公司原料動力廠原油蒸餾車間分別在1987年和2002年發生物理爆破事故造成的渣油泄出。而對于這兩起事故,蘭州官方以及威立雅水務集團都是知情的。而且,這兩起事故并非蘭州自來水安全的唯一隱患。根據財新的記者了解,早在2007年,威立雅集團就向蘭州方面匯報了自流溝頻頻受到人為污染的情況。《蘭州晨報》也曾報道,甚至有人將大量生活污水和糞便排入自流溝。
4月12日,蘭州市威立雅水務集團苯超標的水廠4號自流溝附近仍臭味刺鼻
清除渣油污染并不是技術難題,即便在上世紀80年代,也有能力及時清污
針對官方通報的原因,此次蘭州自來水污染是源自上世紀80年代的渣油泄漏事故。而在蘭州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所長、蘭州市專家咨詢服務團成員張明泉看來,這樣的事故當年就可以處理,拖延至今難以理解。“按照規定,大城市及特大城市的水源地主輸水管道周邊50米內是保護區,不允許有任何與飲水設施無關的工廠、企業存在,而一旦出現可能影響到飲水安全的污染物更是要及時清除。” 在張明泉看來,即使以上世紀80年代的技術,采用客土法(土壤修復)以及換水(油污染治理)完全可以及時清除污染,更不要說如今還有更多更先進的處理技術。 他認為,從這個角度來看,污染持續20多年仍未排除難以理解。此外, 張明泉還表示,由于對渣油泄漏污染處理的拖沓,使得泄漏不僅僅會污染自來水管道,還會使得渣油下滲污染地下水,而地下水污染一旦形成其影響就將持續幾十年甚至上百年。
城市規劃不科學,使得蘭州的自來水管線只能橫穿重化工區
從城市規劃的角度看,蘭州到今天才出這樣的污染事故,已經是個奇跡。從規劃上來說,西固區是蘭州這個長條帶狀城市的上水區,黃河由這里入城,流過整個蘭州。但這里卻被規劃成為重化工區,蘭化、蘭煉、蘭鋁等諸多高污染大企業集中在這里。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圍繞它們,又衍生出一串高污染的小企業。而被污染的自流溝有相當一段就設立在西固區,緊挨著某些石化管網。如果管線和自流溝封閉性不足的話,油污污染自來水,幾乎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蘭州市威立雅水務集團苯超標的水廠自流溝設置示意圖
此外,張明泉還發現,蘭州唯一自來水取水口上游很短的距離內周邊就分布有以中核集團公司504廠為代表的核工業企業和以中石油蘭州石化公司、蘭州維尼綸廠為代表的化工企業數十家,甚至在蘭州市區水源地準保護區內就存在2個工業排污口,另有14個生活排污口。
地方政府治理污染熱情不高,對涉事官員和污染企業處罰力度也不大
蘭州市的自來水官網是上世紀50年代前蘇聯援建的項目之一,老化嚴重,可政府財政卻未保證建設投入。根據《21世紀經濟報道》的報道,2007年威立雅收購蘭州供水集團45%的股份時,高達17.1億元的股權轉讓款中有約6億元的國有股轉讓款被政府拿走,然而這些錢卻完全并沒有用于供水管網建設。因為蘭州市政府徹底把歷史包袱甩了出去,要求新的合資公司負責全面對網管系統進行改造。
此外,雖然2008年蘭州曾斥資1.5億整治過自流溝周邊環境,但收效也不明顯。在去年中石化青島爆燃事故后,國務院也曾要求排查化工管道安全,現在看,蘭州的排查工作顯然不到位。
而地方政府在環保治理上熱情不高的原因也不難理解。一方面對于違規企業,罰金往往只有幾十萬,沒有太大的威懾力。另一方面,地方官員的升遷與環保的關系不大。根據清華大學和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學者們對中國283個城市的市委書記和市長業績及升遷資料的分析,數據顯示,如果地級市的黨政一把手任內在改善環境上的錢越多,反而越不利于他們的升遷。即便近年來實施的是所謂環境問題的“一票否決制”,在實施中主要針對的也是環境官員,一旦出現嚴重環境污染事件,少有當地黨政主要負責人被問責。
地方政府和涉事國企之間就責任相互推諉,也提高了治理的難度
大型國有企業的環境污染事件不僅不是首次,而且問題多多;不僅是污染問題嚴重,而且公眾和環保部門還常常對其無可奈何。美國學者、亞洲研究會主任Elizabeth Economy(伊科諾明)就曾評論道:在中國,國企污染不是什么特例,而是一種常態。數據也證實了這一點,根據環境保護部新近公布的《2009年國家重點監控企業及污水處理廠全年監測超標企業名單》透露,2009年環保部監測的7043家國家重點監控企業中,有2713家企業超標排污,約占監測總數的四成,而其中有相當部分都是國有企業。對于此次事件涉及的蘭州石化,早在2011年5月18日,東方早報就曾發表《蘭州政企博弈七年,拆不掉地下“定時炸彈”》,報道記者鮑志恒強調“蘭州石化與當地政府均認為責任在對方,該隱患一直未得到妥善解決”。
實際上,由于大型國企身上濃重的行政色彩,并控制著重點領域的市場資源,這導致大型國企成為各個極力追求GDP政績的地方政府追捧的對象,地方政府普遍會攀附這些財大氣粗的企業,這也使得央企在地方政府面前具有心理優勢。而動輒幾十億元的項目投資也很容易讓地方政府在生態環境、社區影響等負外部性問題上做出讓步,默許甚至縱容大型國企在投資生產過程中的不正當行為。
對于政府與污染國企博弈的影響,《紐約時報》就在2013年3月的一篇報道中一針見血的總結到“內斗,中國治理環境污染之誤”。
蘭州西固區內有包括蘭州石化在內的大量國有化工企業
對管道安全的檢測缺乏規范,檢測結果存在舞弊空間
3月6日,蘭州市民曾發現自來水出現異味。至3月16日,蘭州市政府仍每天向市民通報水質數據。當時,蘭州市政府協調了甘肅省水利廳、黃委會,調水增加黃河上游水流量,并對黃河上游涉水的47家企業、23條河洪道進行了全面排查。蘭州威立雅水務公司還對內部設備、工藝和供水管網進行了檢查。現在看來,這些檢查并沒有真正解決問題。
實際上,對于相關企業的管道的檢測,并沒有明確和強制的標準。根據《第一財經周刊》對業內人士的采訪發現,“政府要求做哪些‘體檢’,體檢提供哪些數據、哪些項目,這都是政府要監督的,但我們沒有聽過政府哪個部門來我們企業強制檢查。一些管道運營企業,如果沒做年檢或者年檢了但有些項目沒檢,就有了安全隱患。”而在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能源方面的學者涂建軍看來,由于工廠的監測設備的不規范,這些檢測結果是可以被操控的。
更值得警惕的是類似的“隱疾”,蘭州并非孤例
面對類似的頑疾,蘭州并不是中國孤例,南京、廈門、青島等城市同樣存在。事實上,此次蘭州水污染事故與不久前發生的中石化青島爆燃事故如出一轍:輸油管道泄漏的原油“串入”了市政水渠,在形成密閉空間的暗渠內油氣積聚遇火花發生爆燃。
而環保部在2006年公布的一次全國石化項目環境排查顯示,全國7000多個化工化石建設項目中,81%布設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區等環境敏感區域,45%為重大風險源。6000多家化工廠在全國各大城市的主城區和取水區開工、排放。而直到2014年的今天,對已經遠遠超過6000家的企業名單、位置、環境風險評估,以及相應的處理辦法,公眾仍不得而知。
更令人擔心的是,除了這些化工企業,城市規劃部門本身對地下管線了解也不清楚。根據中國城市規劃協會地下管線專業委員會調查,全國大約有70%的城市地下管線沒有基礎性城建檔案資料,地下管線家底不清的現狀普遍存在。而對于這些現狀不明晰,缺乏資料的管線來說,一旦發生事故,甚至查明原因都是個問題。
此外,飲用水突發性污染還有很強的隱蔽性,有些污染很可能發生的無聲無息。清華大學環境學院飲用水安全研究所所長劉文君就認為:“即使是飲用水突發性污染多次成為關注焦點,其頻率也很可能被低估。近幾年發生的幾起重金屬污染事件,如2008年株洲、湘潭鎘污染事件,2012年2月廣西龍江鎘污染事件,包括此次蘭州苯污染事件,每次都是偶然發現。”在她看來,“兩次定期檢測之間的發生污染,往往不能被察覺。”
蘭州自來水污染源頑疾難治的背后是當地政府、威立雅水務和相關石化企業的“內斗”,而在各方為了各自利益的博弈之中,公眾飲水安全的訴求卻被忽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