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水超標排放,公開致歉就能減罰50%?柔性政策為環保執法帶來何種影響?
時間:2022-04-13
來源:廣州市生態環境局、企業污廢水圈、中國水網
作者:焱焱
據中國水網獲悉,近日,廣州市生態環境局首宗環境違法案件完成公開道歉,此次公開道歉完成后,白云分局將進一步審查并視情按罰款標準的30%~50%降低處罰。
近日,據中國水網獲悉,廣州市生態環境局“公開道歉”專欄刊登了一則環保公開道歉承諾書,這是白云區某公司按照廣州市生態環境局白云分局指引完成的全市首宗環境違法案件公開道歉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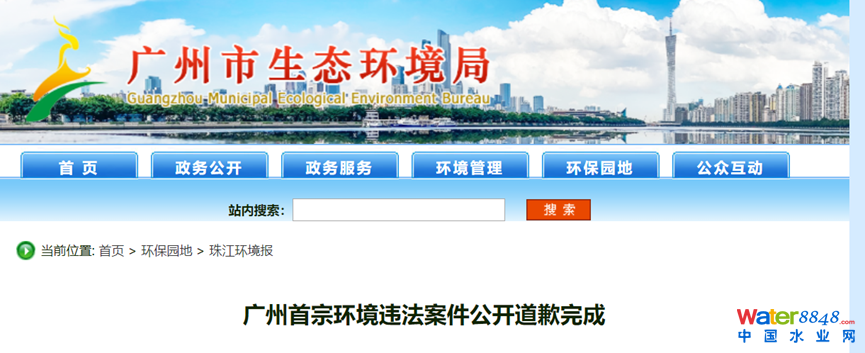
依據廣東省生態環境廳,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的《廣東省生態環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規定》(以下簡稱《規定》),部分排污企業適用“生態環境違法行為公開道歉承諾從輕處罰”制度。3月2日,上述企業在廣州市生態環境局“公開道歉”專欄刊登公開道歉承諾書,承諾要守法經營,提高企業守法意識與環境管理水平,切實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白云分局將進一步審查并視情按罰款標準的30%~50%降低處罰。
道歉是否減罰,還得看從重、從輕標準
看到廣州市排污企業道歉減罰的首個案例,或許部分“排污”大戶對道歉充滿興趣,但道歉減罰并不適用于所有企業。依據《規定》,符合以下條件企業應當依法從輕或減輕處罰:
(一)屬初犯,且違法的主觀惡意小,造成的環境污染輕微、生態破壞程度較小或者尚未產生危害后果的;
(二)主動改正或者及時中止違法行為的;
(三)積極配合案件調查、主動陳述全部違法事實的;
(四)已獲環評批復同意的,具有公益屬性的學校、醫院、市政道路、橋梁或其他基礎設施等的建設項目,且已落實環境保護措施或已接駁市政管網的;
(五)已及時足額投保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
(六)在最近一次企業環境信用評價中被評為“綠牌”的;
(七)違法行為發生在重大疫情控制和預防的關鍵時期,且生產經營內容為研發、生產或提供與疫情防控相關的技術、產品或服務的;
(八)違法行為發生在重大疫情控制和預防的關鍵時期,且積極參與重大疫情防控工作,或者對疫情防控作出較大貢獻的;
(九)主動參與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磋商并積極履行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和修復義務的;
(十)生態環境法律法規規章規定的可以從輕處罰的其他情形。
從上述道歉減罰的標準中,也能看出,該項制度的適用范圍僅限初犯,對于多次違法的企業并不適用,甚至部分存在以下情節的企業,將會加大懲處力度:
(一)在案件查處中對執法人員采取威脅及要挾(包括口頭)、辱罵、毆打、恐嚇或者打擊報復等暴力或脅迫行為,或者以其他方式妨礙、干擾或者拒不配合現場檢查、監測或調查取證的(包括提出不合理要求等方式);
(二)違法向環境排放或傾倒危險廢物、含重金屬的污染物等有毒有害物質的;
(三)違法排污持續或累計時間超過20天,其他違法行為持續或累計時間超過3個月的;
(四)經責令改正或者責令限期改正,但拒絕改正或者逾期不改正、或者繼續實施違法行為的;
(五)造成跨行政區域(區級以上)環境污染后果的;
(六)涉及污染大氣環境的違法行為處于重污染天氣預警期間,或者處于特殊或重大活動期間的;
(七)有轉移、隱匿、使用、毀損、變賣等擅自處理被依法查封、扣押的設施、設備行為或者擅自撕毀封條的;
(八)違法行為造成突發環境事件或者對生態保護紅線內、自然保護區、飲用水水源保護區、風景名勝區、森林公園、重要濕地、基本農田保護區、文物保護單位等環境敏感區域造成重大影響的;
(九)近二年以來被查實的有效舉報投訴達三次以上,或者引發群體性事件,或者造成惡劣社會、輿論影響的;
(十)近二年以來因同類環境違法行為被處罰三次以上的;
(十一)發生在重大疫情控制和預防關鍵時期的偷排偷放、惡意排污、監測數據弄虛作假,以及涉疫情醫療廢物、醫療廢水等行為,侵害群眾健康、群眾反映強烈或嚴重污染環境的;
(十二)生態環境法律法規規章規定的應當從重處罰的其他情形。
為何制定“道歉減罰”的柔性環保政策?
從2014年生效的“新環保法”,到近年來的中央生態環保督察都釋放環保執法力度正在逐漸強化的信號。廣東省出臺的《廣東省生態環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規定》中柔性執法似乎和近年來環保執法主流論調略有不同,不禁讓人疑問道歉減罰制度制定的初衷是什么?
事實上,關于環保執法過嚴問題,2014年E20水網固廢網曾發布《環保觀察:莫讓環保執法變成“罰款”執法》,文章中曾探討,排污罰款,對于某些大企業來講,每日處罰金額可能遠小于其治污需要的費用,更小于違法生產賺得的利潤;而對某些小企業來講,最終的罰款額可能超出其承受能力,甚至“資不抵罰款”。
據企鵝污廢水圈報道,從《規定》出臺后,企業在環保方面投入將由被動轉為主動。一位環境違法企業負責人表示,“因為我們違法面臨高達50萬元的罰款,這對于我們這種規模不大的企業來說是致命打擊,現在有這樣一個政策,給了我們一個機會,我們愿意直面錯誤,向市民誠懇地道歉。”
廣東對環保企業柔性執法的考慮初衷,也是建立在2016年《深圳市環境行政處罰裁量權實施標準(第三版)》首創“違法者主動道歉承諾從輕處罰制度”基礎之上,而該制度設立的初衷主要是為了解決以下三方面問題:
對企業而言——部分有整改意愿的企業因處罰額度較高導致資金困難從而減少環保投入;部分違法企業高層管理者僅憑罰款也缺少體驗式教育,難以觸動靈魂。
對執法者而言——由于推行零自由裁量權的定額罰款,剛性高額罰款使處罰中的申辯、聽證以及處罰后的復議、訴訟程序增加,影響執法效率,耗費社會成本。
對公眾而言——環境執法相對專業和封閉,直達公眾的鮮活案例少,對環境執法知曉度低、參與度不高。而公開道歉承諾,可以讓“公眾關注”倒逼污染企業落實整改。
對上述問題的考慮,并非建于空中樓閣,以往也有切實可考的案例發生。例如西寧第一、三污水廠曾因為進水嚴重超標,導致設備受損,出水不達標,從2013年12月開始至2014年8月,水廠已經收到9張罰單,總計罰款300多萬元。水廠將情況反饋至環保部門,希望協助嚴查進水,并撤銷罰款,但一直未收到相應回復。
一位不愿署名的行業專家接受《中國水網》采訪時介紹,從職責范圍來講,環保部門有對污染過程的監管責任,但很多時候,他們只能對結果負責。按日計罰,通過加重經濟處罰,在一定程度上,會促進環保部門對結果的執法力度,但對過程的執法,卻沒有更好的規定。專家對此認為,從監管的角度,環保部門對于超標排放進行罰款沒有問題。但在罰款同時,環保部門也有義務積極配合污水廠尋找進水超標污染源,并加強對污染源企業進行監管和處罰。如果只僅僅通過對下游企業罰款進行倒逼,忽視或不進行前端監管,效果并不一定會如其所愿,反而會成為“為罰款而罰款”。
道歉減罰,在生態環保治理中到底有何成效?
1、企業環境違法行為改正率明顯提高
相關部門負責人說道,該制度的實施,有利于督促違法企業用沉甸甸的責任來體現企業的擔當,用實實在在的效果來檢驗道歉的誠意,用環境質量的改善來兌現環保承諾,更加規范自身的環保行為,遵守法律法規。
從數據來看,深圳作為制度試點城市,自2016年至2021年累計已有1270家違法企業在深圳主流媒體公開道歉承諾,均在作出處罰決定前自覺完成整改。
其中,2020年、2021年分別有53家、48家企業公開道歉承諾,減免處罰金額分別為469.5萬元、487.4萬元,均占當年總處罰金額的4.3%。
公開道歉承諾企業中,2020年再次違法企業僅6家,2021年僅2家,企業守法意識明顯增強。
2、行政處罰的教育作用明顯體現
公開道歉承諾引起了企業法定代表人及高層管理人員的高度重視,按照制度設計,他們從提交道歉承諾申請、審定道歉承諾書和簽名登報道歉承諾等多個環節都全程親身參與,教育作用得到有效發揮。
同時,公開道歉能在行業內和社會上產生強烈反響和震動,促進公眾參與和監督。
值得一提的是,公開道歉的企業主要是守法意識和能力相對薄弱的小微企業,該制度一方面實現了對企業的守法指導和幫扶,另一方面也緩解了行政處罰給企業造成的資金困難,助力小微企業綠色健康發展。
環保觀察:莫讓環保執法變成“罰款”執法
時間:2015-10-16 17:03
來源:E20環境平臺
作者:谷林
今年生效的“新環保法”,作為一部“長了牙齒”的環保法律,讓環境保護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力度和信心。陜西天價罰單,更被稱為新環保法的首例“按日計罰”范例,獲得行業廣泛關注,贏得一片叫好之聲。不少媒體也評論認為:這種“按日計罰”,不僅體現了法律的嚴肅性,也可以極大地震懾一些違法污染企業。
但在叫好聲外,其中的問題也引發一些質疑:
根據媒體報道,近些年來,越來越多的實例表明,一些地方的環保局本來平日里沒有保護好環境,卻一有污染事件發生便立馬上去罰款,大發一筆橫財。
即使不是如此,排污罰款,對于某些大企業來講,每日處罰金額可能遠小于其治污需要的費用,更小于違法生產賺得的利潤;而對某些小企業來講,最終的罰款額可能超出其承受能力,甚至“資不抵罰款”。
同時,從處罰本身,按日計罰,有可能會讓環保執法變成“罰款執法”。如陜西事件,從1月8日到3月27日,雖然原先20萬元罰款變成了1580萬元重罰。但在環保部門首次作出停產整治的決定后,這家企業仍繼續生產了79天,人們的生活環境因此被繼續污染了79天。對污染企業進行罰款不是目的,目的是為了讓其不再違法排污。如果違法排污總是不能杜絕,罰再多的錢恐怕也沒有意義。
一位不愿署名的行業專家接受《中國水網》采訪時介紹,從職責范圍來講,環保部門有對污染過程的監管責任,但很多時候,他們只能對結果負責。按日計罰,通過加重經濟處罰,在一定程度上,會促進環保部門對結果的執法力度,但對過程的執法,卻沒有更好的規定。
而對于污水處理廠這樣的治污企業來說,這種結果導向卻可能產生另外的問題。
今年7月,因為出水水質超標,國中水務秦皇島公司收到1299.32萬元罰單。對此,國中水務在公告中稱,此次超標排放的主要原因為進水水量超負荷,進水質量惡化,進水水質遠超設計標準。后續,他們將全力協調地方政府盡快解決問題,或通過申請行政復議或提起行政訴訟的方式依法維護公司權益。
西寧第一、三污水廠,也面臨這樣的問題。據介紹,因為進水嚴重超標,導致設備受損,出水不達標,從去年12月開始至今年8月,水廠已經收到9張罰單,總計罰款300多萬元。水廠將情況反饋至環保部門,希望協助嚴查進水,并撤銷罰款,但一直未收到相應回復。
前述專家對此認為,從監管的角度,環保部門對于超標排放進行罰款沒有問題。但在罰款同時,環保部門也有義務積極配合污水廠尋找進水超標污染源,并加強對污染源企業進行監管和處罰。如果只僅僅通過對下游企業罰款進行倒逼,忽視或不進行前端監管,效果并不一定會如其所愿,反而會成為“為罰款而罰款”。
中共廣東省委黨校法學部程雨燕教授在接受《中國青年報》采訪時曾說,執法的目的的不是罰款,不能‘為了罰款而罰款’,而是為了改善環境。
中國甘肅網以及新華社每日電訊等媒體也曾刊登主題評論認為:罰款不過是體現管理的作為,而不是真正督促解決排污問題。作為環保部門,不能一罰了之,更不能為了能罰到更多的款而對企業的違法污染行為放任不管,而是應該及時對企業進行督促改正。遏制企業違法排污,不能光算經濟賬。
如從保護環境出發,有一些地區的經驗值得借鑒。如,面對同樣的進水超標問題,寧波一些污水廠與環保局建立了聯動機制,成立水質超標監督隊,一旦發現出水或進水超標,即啟動環保排查,一起尋找原因,加強治理。
2013年5月,遼寧省環保廳與遼寧省公安廳制定并下發文件,建立公安、環保環境執法聯動協作機制。遇到環境違法案件,主動提請公安機關提前介入調查,協調公安機關建立案件信息共享機制,實行環境違法案件信息互聯互通。組成“打擊環境違法行為特別行動隊”,實現執法聯動、聯合督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