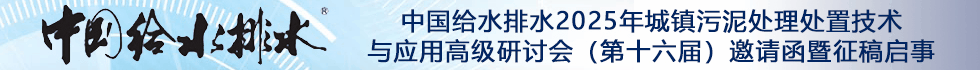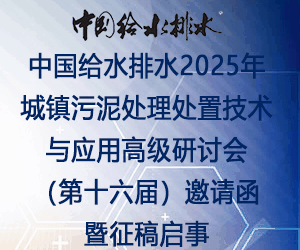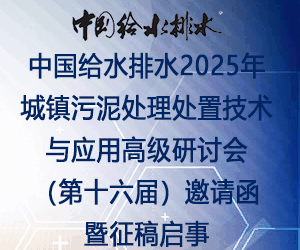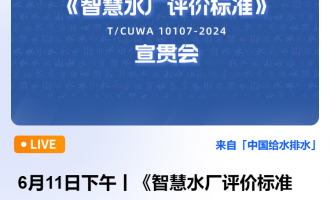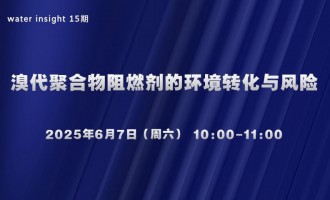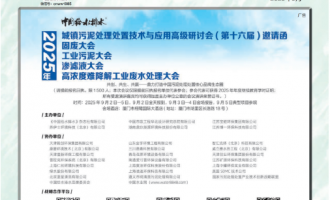從垃圾分類到循環經濟 超大城市固廢治理方案
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深入發展的關鍵階段,固體廢棄物(下稱“固廢”)年產量已突破百億噸規模,而傳統填埋處置方式不僅造成環境污染、占用土地資源,更導致大量溫室氣體排放。2018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無廢城市”建設試點工作方案》,提出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深圳等11個城市入選首批試點。隨著《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和《“十四五”循環經濟發展規劃》等國家戰略的深入推進,固廢資源化已成為實現減污降碳協同增效的重要突破口。
我國“無廢城市”建設重點聚焦工業固廢、農業廢棄物、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四大領域,其中城市生活垃圾治理尤為關鍵。深圳作為管理人口超2000萬的超大型城市,面臨土地資源緊張、環境承載力接近極限等挑戰。據統計,深圳年均產生生活垃圾約1200萬噸,建筑垃圾超過1億噸,傳統填埋方式已難以為繼。在“無廢城市”建設背景下,深圳市通過系統性創新,構建了垃圾分類、精細化處置、多方協同和動態政策調控的全鏈條治理體系,積極探索“政府引導、市場主導、科技支撐、公眾參與”的多元共治模式,為超大城市固廢治理提供了可復制的解決方案。
垃圾分類賦能城市可持續發展,深入發掘資源價值與環境效益
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加快,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持續攀升,預計2030年將達到5.85億噸。生活垃圾是放錯位置的資源,具有資源與環境雙重屬性:經科學分類和合理利用能夠轉化為再生資源,如若處置不當則會造成環境污染,危害人類生活環境和健康。2019年起,我國全面推行“四分法”分類標準,將生活垃圾分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廚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深圳市作為首批“無廢城市”試點城市,通過智能回收箱、綠色賬戶等創新舉措,實現了42%的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為超大城市垃圾分類提供了示范樣本。
垃圾分類政策的有效推廣能夠顯著改變進入城市市政系統的混合垃圾組分構成。例如,餐廚垃圾的有效分離能夠使混合垃圾熱值提升15-20%,這一改變既能夠提高焚燒發電的效率,同時能夠減少填埋產生的甲烷排放,為整個生活垃圾處置系統帶來碳減排效益。另一方面,分類后混合垃圾中塑料組分占比顯著增加,但由于當前城市回收體系中的塑料垃圾普遍存在破碎、混雜等問題,傳統機械分選技術的回收率不足40%,嚴重制約了資源化價值。混合垃圾中塑料組分含量對評估城市生活垃圾處理過程的環境表現方面至關重要,因此在后續管理中應通過技術創新和精細化管理,推動廢棄物處置和資源回收兩網融合,充分釋放可回收垃圾的資源價值,實現環境保護與資源再生的協同發展。
精細化處置結合智慧化管理,實現固廢治理“減污降碳”協同增效
垃圾分類政策的實行使后端形成更為復雜的物流體系,如果后續垃圾資源化處置水平不足,則分類收集的形式和范圍也將受限。過去10年間,我國生活垃圾管理體系正經歷從“無害化處置”向“資源化利用”的戰略轉型。通過持續推進垃圾分類,我國已實現99%以上的無害化處理率,但傳統的填埋和焚燒模式仍難以滿足新時代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需求。深圳作為“無廢城市”建設試點,創新性地構建了“精細化分類+智慧化處置”的新型管理模式,將集中式末端治理處置與精細化資源化利用技術結合,為社會發展創造更豐富的資源二次利用價值。
深圳模式的核心在于技術創新與系統優化。首先,開發智能調度系統實現垃圾物流精準匹配,在多個垃圾管理環節之間建立動態聯系,為各類廢棄物匹配最優處置路徑,控制垃圾處置系統碳排放總量;其次,采用厭氧消化與熱解氣化等組合工藝,同步處理廚余垃圾和塑料制品,在確保無害化的同時提升資源轉化率;再者,建立全流程數字化監管平臺,實現從源頭投放到終端處置的可視化管理。這種創新實踐能夠打破“先污染后治理”的線性思維,通過末端處置與資源化技術的系統耦合,構建了減污降碳協同增效的新范式。它不僅解決了“垃圾圍城”的困境,更為超大城市固廢治理提供了可復制的“深圳方案”,為我國循環經濟建設提供了重要參考。
破解固廢循環利用的“三角困境”,構建多主體合作機制
當前我國固廢管理正經歷從“末端治理”向“全流程管控”的重要轉型,但各主體間的利益訴求差異形成了現實阻礙:政府側重于提升環境效益,產廢企業需控制成本,利用企業則受制于原料質量和技術瓶頸。這種“三角困境”導致資源化產業鏈條難以有效銜接,使得我國固廢資源化率長期徘徊在30%左右,與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普遍60%以上的資源化率相比,存在明顯差距。破解這一困局需要在政府、產廢企業和固廢資源化企業之間建立協同機制,促進不同主體間的協同合作與市場可持續發展。
應對固廢治理挑戰,政府應首先發揮主導作用,通過補貼、稅收優惠與制定排放標準等“激勵—約束”并重的政策組合引導企業積極參與;產廢企業則需不斷完善內部分類體系,推動形成固廢資源化利用的細分市場;利用企業則應加大技術創新投入,提高資源轉化效率。這種協同體系的建設不僅需要制度創新和技術突破,更有賴于全社會環保意識的提升。只有當各主體形成發展共識,才能真正實現固廢管理的“閉環化”轉型,發揮跨主體協同效應,推動實現建設“無廢城市”建設和循環經濟發展。
差異化的政策與市場調控策略,實現“三位一體”協同發展
固廢循環利用是一個需要政府、企業和市場協同發力的系統工程,需要根據固廢資源化市場的不同發展階段采取差異化的政策組合。通過科學的政策動態調整能夠有效引導市場機制逐步接棒,形成“政策引導—企業響應—市場驅動”的良性循環,推動提升固廢資源化利用效率。在固廢治理初期,市場機制尚未成熟,需要政府構建“激勵—約束”并重的政策組合打破僵局,如實施階梯式收費制度,對分類垃圾減免部分處置費;或設定再生材料強制使用比例,創造市場需求等,通過“政策孵化”效應撬動市場,從而提升企業合作意愿。
隨著回收渠道的完善和市場機制的成熟,政策重心應逐步轉向制度創新,通過制度設計,將環境正外部性轉化為市場內生動力,實現從“政府主導”向“市場驅動”的平穩過渡。政府作為宏觀調控者,應持續優化激勵政策,構建科學的績效評價體系,對全流程表現突出的單位給予支持。同時要主導回收渠道建設,設立專項基金支持技術創新,通過綠色采購政策培育市場需求。例如深圳寶安區試點將建筑垃圾資源化的碳減排量納入交易體系,使企業獲得額外收益;同時建立產能監測系統,避免區域性產能過剩。這種動態調整的政策框架,既能解決當前資源化瓶頸,又能為產業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最終實現“政府搭臺、企業唱戲、環境受益”的固廢治理新格局。【本文系深圳市社科規劃課題《雙碳目標下深圳無廢城市建設的碳減排潛力及成本綜合評估研究》(編號:SZ2022B018)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分別為深圳大學管理學院教授、深圳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研究員)
責任編輯:武曉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