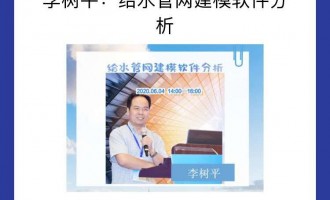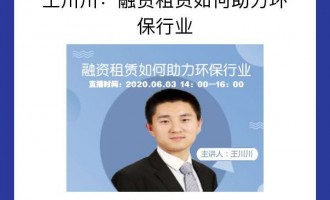研究|偏向中西部的資源配置,沒有遠慮必有近憂
(陸銘在西部一地拍下的一個工業園。在中國,進行大量投資,卻沒有招來什么企業的工業園,呈遍地開花之勢。)
伴隨著經濟增速放緩和地方政府債務累積,中國經濟似乎正在面臨一場如何兼顧效率與平衡的戰略選擇。
但實際上,效率和平衡并非不能兼得。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和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陸銘、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向寬虎,就在2014年第4期《經濟社會體制比較》撰文指出,之所以效率和平衡出現沖突,是因為在中國仍存在著阻礙勞動力充分流動的制度障礙,主要是戶籍和土地制度。文章題為《破解效率與平衡的沖突——論中國的區域發展戰略》。以下為經作者授權的摘編。
研究者認為,經濟理論和國際經驗均證明,在一個國家內部,如果沒有勞動力流動的阻礙,經濟向少數地區的集聚和地區間差距的擴大只是階段性現象,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提高,經濟集聚的同時,地區間差距會逐步縮小。而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在堅持有利于欠發展地區持續發展的轉移支付政策的同時,促進勞動力充分自由的流動是兼顧效率與平衡的戰略選擇。
從理論上說,要實現平衡發展(人均收入差距縮小)的目標,有“動錢”和“動人”兩條路可走。在人口不能充分流動的情況下,中國在過去采用“動錢”的方式,給欠發達地區更多轉移支付和投資,提高其經濟總量。
而“動人”則是指去除人口跨地區流動的障礙,來實現人均意義上的平衡:欠發達地區人口向發達地區流動,一方面減緩發達地區的工資增長,另一方面欠發達地區的人均資源占有量提高。如果考慮經濟集聚的力量,則發達地區人口流入不會帶來人均收入水平下降,而是會提高發達地區的收入水平。如果再考慮公共服務提供的規模經濟效應,則人口自由流動條件下實現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雙贏的可能性更高。
對中國整體而言,全球化、知識經濟和服務業發展使得經濟集聚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在不斷增強,這些外在條件的變化使得限制人口流動的潛在損失越來越大。因此,通過“動人”的方式來實現地區的平衡發展,具有較強的效率優勢,并且這一優勢可能越來越強。
反過來,不“動人”而只“動錢”,不僅會導致經濟效率損失,如用地效率低下、投資低效率等,在地方政府之間存在激烈的GDP競爭的情況下,傾向于內地的資源配置還孕育著較大的金融風險。當前,中國內地省份的地方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高于東部省份。
研究者指出,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規模、國土縱深如此之大的國家,內陸地區產生若干服務于內需的次中心城市也是符合經濟規律的。但當前內陸地區工業發展的不合理之處在于發展方式,即速度、布局和結構問題,投資增長過快,布局過于分散,結構過于重型化的現狀亟需糾正。
出于效率的考慮,內地的工業應優先考慮布局在內陸大城市周邊,形成區域性都市圈。而目前一些內地省份工業發展的現狀是開發區遍地開花,縣和縣之間在招商引資上也存在惡性競爭,結果是在一個省范圍內也難以實現工業集聚發展,大城市的經濟輻射作用沒有很好地發揮,不少省份甚至出現了人口集聚度下降的現象。
研究者特別強調,內地的工業發展必須是以存在一定量的農業人口和依賴于本地資源的從業人員(如旅游、自然資源產業)為前提的,因此,有效的工業發展或者是配套這些產業的(如農產品加工和資源產品加工),或者是服務于當地一定范圍內的生活需求的(如就近銷售的服裝和食品),或者是生產少數不依賴于海運的產品(如芯片、軟件等)。
依據其他的研究,2004-2005年之前,地區間差距整體呈現上升趨勢。2005年之后,地區差距呈現收斂跡象。這個轉折是如何發生的,其背后是什么?
研究者認為,這和政府在平衡地區發展上的各種努力分不開。每個地方每年新增的建設用地指標是由中央控制的,因此地方的土地供給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央的指標分配格局和對地方執行情況的監管力度。中西部省份土地供給占全國土地供給的比重在2003年之后明顯上升。
2003年后,開發區的設置也被作為支持內地發展的手段。之前,各地地方政府出于發展本地經濟的動機,進行著激烈的招商引資競爭,廉價土地是競爭的主要手段之一。在中央和地方信息不對稱的格局下,地方政府的實際用地往往超出中央規劃。為控制“開發區熱”和建設用地的過度擴張,國家在2003年7月底開始發文,對開發區和建設用地進行清理整頓。這一輪清理整頓中,全國開發區數量由6866家減少到1568家,減少77.2%,規劃面積由3.86萬平方公里壓縮到9949平方公里,減少74.0% 。在開發區清理過程中,對中西部地區、東北老工業基地的資源枯竭型城市、部分老、少、邊、窮地區的開發區,在入園企業個數、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產業發展規模等具體審核條件上給予了一定傾斜。
基于中國規模以上企業調查數據,研究者統計了每一個城市在每一年中開發區內企業在全國開發區內企業數量中的比重,并繪制了城市開發區內企業所占比重與該城市到香港、上海、天津這三大港口的最近距離的關系圖。結果發現,在距離大港口500公里以外的地區,開發區企業數量占全部開發區企業數量的比重在2003年之后是明顯上升的。
另外,中西部省份獲得的轉移支付在全國總量中的份額在2003年之后持續上升。從微觀企業層面,也可以看到類似現象。在所有被補貼企業中,中西部地區被補貼企業數量占比和補貼收入總額占比大約在2003年前后出現了拐點,之后均有所上升。
尤其值得重視的是,不管是從城投債發債的支數還是規模來講,內地省份所占比重近年來總體處于上升趨勢,在2012年,這兩個比重均已超過50%。相對于其現有經濟規模和未來經濟增長的前景,內地省份日益增長的負債規模孕育了不容忽視的債務風險。
研究者指出,經濟資源在區域間的配置方向出現拐點后,也相應地引起了勞動力市場上“拐點”的出現。2003年之后,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工資的明顯上漲,這曾被認為是城鄉二元經濟中開始出現勞動力短缺的表現,然而這也可能是政策干預的后果。
經濟資源向中西部的傾斜,帶動了中西部的投資和經濟增長,勞動力需求也相應上升。在東部省份,土地供給的相對收緊推動了東部地區的房價上漲,進而推動了工資的顯著上升,這種工資上升的機制主要是在2003年之后出現的。
對中西部投資引致的勞動力需求上升,以及惠農政策對農民工保留工資的推升,降低了勞動力主要流入地——東部地區和大城市——的勞動力供給,加速了其工資上漲。2003年前后區域平衡政策的拐點和勞動力工資上漲的拐點同時出現,不應被作為“巧合”來對待。
如果對于行政配置資源的效率損失的擔憂是正確的,那么,可以預期的是,效率損失的體現也應該在2003年前后出現拐點。研究者進而利用1999-2007年間制造業企業的數據(以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的數據,計算全要素生產率,即TFP),對此進行了驗證。
研究者發現,2003年后,按就業份額加權平均的總體TFP的增長率的確呈現下降趨勢。雖然TFP增長率在年和年之間有波動,但在2003年以前,其主要趨勢是上升的,2003年到2007年之間,TFP的增長趨勢卻中止了。這一時間的拐點剛好和前文中描述的政策拐點的時間吻合。
另外 ,研究者分析數據指出,2003-2004年的清理整頓,對沿海地區的制約作用不僅在于有利的政策被取消,還在于清理整頓過程中的地區偏向使得沿海地區有更多企業蒙受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損失。
政策扭曲加強的后果,則是資源配置效率的下降。研究者采用TFP的標準差來度量資源在企業間的配置效率,發現在2001年以前,TFP標準差總體上是下降的,但在2003年以后,卻經歷了一個較為明顯的上升過程。2003年以后TFP標準差的上升,反映了中國整體資源配置效率惡化。
研究者進一步以地區分組計算的結果是,全國層面TFP離散度的增加,從地區維度上來看,主要源自于中西內部的資源配置惡化。而東部地區集聚趨勢減緩而導致東部內部資源配置效率降低這一機制并未發生作用。
從數據中,研究者也發現,出口部門在這十年期間資源配置效率一直是在優化的,這成為優化整體資源配置的一個重要力量,但這一優化力量由于出口企業數量占比在2004年后下降而有所變弱。
而導致整體資源配置惡化的最重要原因,是中西部地區內部的資源配置效率惡化,其拐點大致在2003年前后。從2002年開始,國有部門的資源配置效率開始惡化。由于國有部門在經濟中的比重下降,因而,在所有制和地區這兩股使得總體資源配置效率惡化的因素中,中西部地區的資源配置效率的惡化對總體配置效率的影響越來越重要。
由此,研究者給出的政策建議是,要在生產要素更有效率地加以配置的條件下,讓經濟和人口進一步向沿海地區和內陸的大城市集聚,同時,地區之間在人均收入和生活質量等方面的差距將最終縮小,從而使中國走上一條“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區域發展道路。在這條道路上,中央政府仍然需要發揮協調地方間關系和促進平衡發展的重要作用。所不同的是,中央向欠發達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應更多地投向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和制約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建設。換言之,在生產要素充分自由流動的前提下,輔之以中央向欠發達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這是一條“動人”和“動錢”相結合的道路。這條道路要求中國必須突破地方政府的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桎梏,在全球經濟的大格局中最大限度地發揮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規模經濟優勢,實現效率與平衡的雙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