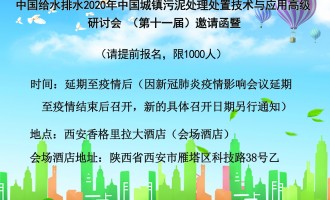那是6年前的事。
位于浦東合慶鎮的上海城投污水處理有限公司白龍港污水處理廠,如今很是風光不僅規模亞洲最大,更是行業環保排頭兵。可蔣玲燕當初去那里的時候,全然另一番景象:污水、污泥,連空氣里都飄著臭味,生產設備老舊、工藝落后……
沒有女孩子會喜歡到這樣的地方工作,但蔣玲燕就選了它。
這個“80后”女孩現在是這家大型企業的副廠長。有人講她運氣好,有人夸她眼光好,都遠遠沒說完整。
惦記“差半口氣”的研究
長發披肩、戴副金絲邊眼鏡,出現在記者面前的蔣玲燕,文氣而干練。
6年前,蔣玲燕即將從同濟大學環境學院研究生畢業,開始“找飯碗”。而此時,白龍港正遭遇“人才危機”總投資22億元的污水廠升級改造和擴建工程在緊鑼密鼓推進,全新的生物處理技術就要取代格柵、加藥除污的落后工藝,處理城市污水的能力和水平將大大提升……可是,瞧著全新的一整套設備,大家面面相覷:老經驗再豐富,眼下也用不上了。
蔣玲燕能攬下這活兒。在同濟大學環境學院讀碩士,把污水變清水正是她專攻的方向。她心里有個疙瘩:“總覺得自己的課題還差半口氣,一些研究還沒出結果,就要畢業了。”
蔣玲燕把心里這個疙瘩稱作“補償心理”,最終簽約白龍港,“補償心理”很起了點作用。“當時廠領導跟我談,說把我當儲備人才,等新項目交付使用,我可以參加調試……”蔣玲燕說,這家地處偏遠、收入不高、工作環境不好的工廠,能吸引她的就是這樣的機會:參與大項目,還有可能讓自己把“差半口氣”的研究做下去。
選擇到白龍港,還因為如今愿意給工科女生機會的企業實在太少,“很多企業招人,都明確不要女生。”不過她也理解,同濟大學許多畢業生,專業對口設計單位,但在設計單位工作,很多時候要下工地,有些工地連個女廁所都沒有,還要接連出差……“如果換我當老板,也只招男生。”
“不能把自己當女生看”
到了白龍港,蔣玲燕就知道,在這里“不能把自己當女生看”。
第一天上班,她帶個照相機,獨自在廠里轉悠。“污水處理有幾種辦法,我們都學過,課題也做過好幾個。但工廠里具體是怎么做的,如何讀儀表參數,如何統計生產報表,如何發現生產異常……都要實際接觸了才知道。”蔣玲燕拍下各種生產設備,琢磨這兒的工藝流程。
偌大的工廠走一圈,兩小時一晃而過。最初幾個月,為盡快摸熟環境,她時不時來一回這樣的“強行軍”。
2008年盛夏,污水廠改擴建工程進入收尾階段,蔣玲燕著手準備調試新設備,又開始了“強行軍”。有時,她拿著照相機在工地上尋找、記錄施工問題;有時,她頭戴大草帽、身穿工作服、腳蹬套鞋,拿個手電筒,鉆進輸送污水和污泥的渠道來回檢查,“渠道里有沒有殘留的建筑垃圾、各種設備安裝是否到位……”蔣玲燕解釋,“這些細枝末節都要緊,事關今后的生產安全。”她懂技術,必須親手排摸隱患。
這時的蔣玲燕已被提拔為廠長助理,擔任調試小組組長。她身后時常跟著幾十個老師傅當“幫手”。
過去,這家處理污水的工廠只有“生產”沒有“科研”。而蔣玲燕要數據,有了數據才能驗證自己的判斷。她采集污水和污泥,然后做實驗,一次次驗證各項設備是否已調試到位。這讓老師傅們看得新奇。
在她帶領下,僅僅3個月,白龍港的污水日處理能力就達到了200萬立方米的規模,創下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調試紀錄。
這3個月里,白皙的蔣玲燕變得黝黑黝黑。
“我還得學會"吵架"!”
2009年,工作還不滿3年的蔣玲燕被提升為副廠長。新的考驗接踵而至,容易“一根筋”、“認死理”的工科生,要學著適應管理崗位。
那一次,上級環保部門到廠里檢查,負責接待和講解的蔣玲燕吃癟了。當時白龍港的新設備剛投入生產不久,一些儀表的工作狀態不佳,讀數時常不準。蔣玲燕布置了彌補措施:讓工人們每天定時測量水質,用人工方法來校準讀數。
“儀表不會作假,可人會作假。你憑什么不相信儀表的讀數,而相信人工操作?”專家的發問讓蔣玲燕啞口無言。她委屈:“怎么能說我們的工人作假?憑什么就說人工數據不可信?”
但她還是根據上級要求認真整改。不久,儀表的工作狀態穩定了,中控室更加嚴密地監測每一個儀表讀數,還順勢引進了“拐點分析”、“異常數據標注”等精細化管理方式。白龍港的這個做法,后來被推廣到兄弟企業。蔣玲燕親歷“進步”過程,慢慢想明白了:做管理不比搞科研,要多聽各方意見,善于集思廣益、綜合平衡。
“讀大學的時候從來沒想到過,我還得學會"吵架"!”分管著廠里的生產運行,蔣玲燕總得盯牢工程建設公司和各家承包商,一旦新發現了質量紕漏,必須立即找回責任方整改,這時“沖突”在所難免。如何最大限度地維護自己企業的利益,同時把握談判技巧、“見好就收”,是一門藝術。
“我就一句話,讀了工科,又不想自己的書白念,就要吃苦。”如今的蔣玲燕比過去更忙,每天提前1小時上班,還經常加班加點,但她不抱怨能在這里得到自己的發展空間、實現自己的存在價值,她很開心。
本報記者 樊麗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