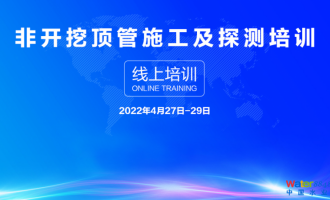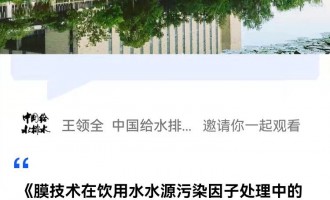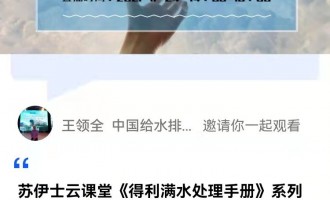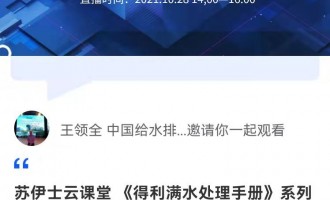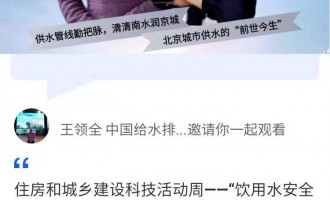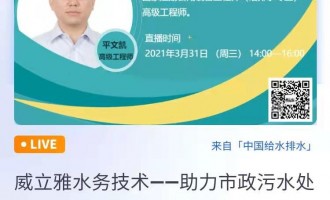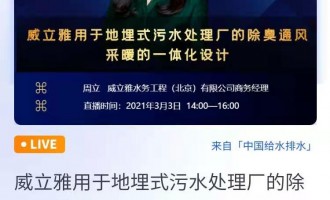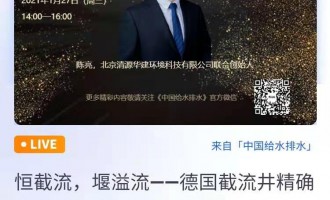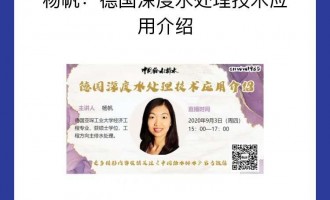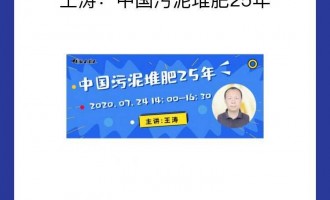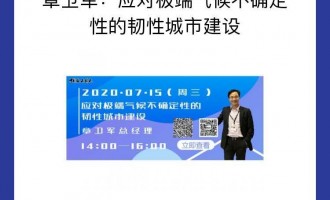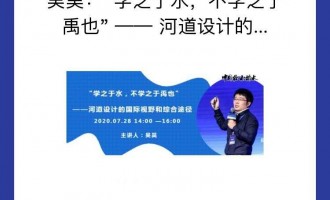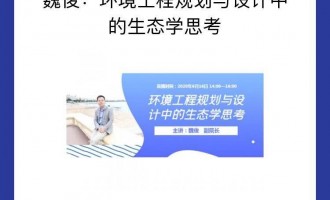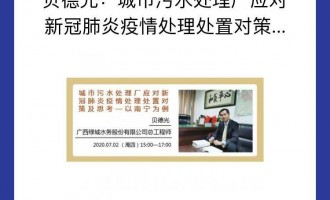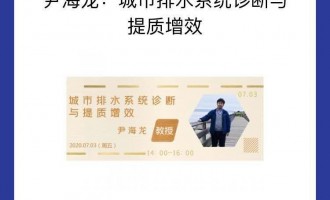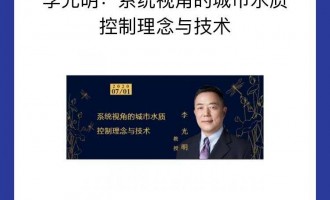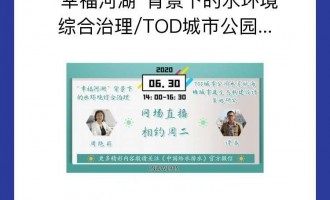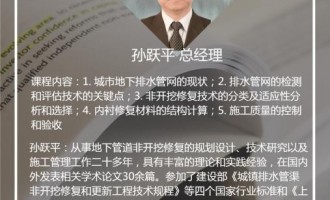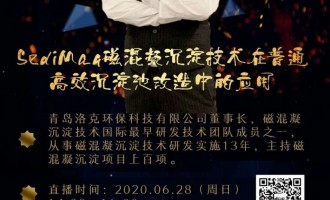“我國是世界上惟一一個提出要建設生態文明的國家。”全國政協委員、環保部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所長高吉喜對本報記者表示,“這既表明國家對生態環境的重視,也說明了我們的環境資源容載力面臨很大挑戰”。
雖然中國的經濟資產在增加,其背后隱藏的代價是生態資產在日益減少,生態欠賬不斷增多。在這種情況下,高吉喜建議對生態資產進行核算和管理。
所謂生態資產主要是指具有物質及環境生產能力的自然資源、生態系統以及經人類利用已經物化在各類生態經濟產品中的資源,價值體現在自然資源、生態服務以及生態經濟三方面。
高吉喜認為,現階段,我國生態欠賬還在擴大,因此應以生態資產管理作為生態文明建設的抓手,建立不同經濟類型區之間的生態補償實施策略,并推動區域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生態欠賬不斷增多
《21世紀》:中國的生態資產現狀如何?
高吉喜:首先,我國的生態資產人均量低下,難以支撐經濟社會發展。總量上看,我國化石能源資產、林木資產等生態資產位居世界前列。但由于人口眾多,人均礦產資源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l/2,人均林木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5。由于我國生態資產人均不足,難以支撐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促使國際經濟貿易中資源產品對外的依存度逐漸增高。
其次,我國的生態資產分布不均,區域流轉量大面廣。以煤炭為例,我國的煤炭資源主要集中在“三西”(山西、陜西、內蒙古西部)和新疆,而煤炭主要消費地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這就產生了煤炭大規模長距離調運問題。有研究測算,我國每年通過鐵路運輸損耗的煤炭達3000萬-4000萬噸。同時,在生態資產消耗、轉移過程中,人們對生態資產輸出區的環境效應重視不夠,致使自然資源豐富的地區其經濟增長往往落后于那些自然資源并不豐富的地區,即出現所謂“資源詛咒”現象。
第三,我國的社會資產增長快速,生態資產卻持續下降。在目前重化工化的發展階段,我們走的依然是一條高能耗、高污染的路子,生態資產下降觸目驚心。
《21世紀》:那么我國的生態資產有管理和核算體系嗎?
高吉喜:目前,在生態資產管理上,我們缺乏系統而完善的統計制度、估價制度和報告制度等相關管理制度,如對生態資產統計客體或統計對象、統計口徑、統計時間、統計報告缺少規范化與標準化,生態資產管理制度不健全。
同時,還缺乏一套生態資產核算評估體系,因此生態資產的家底不清。目前,生態資產評估理論和評估研究方法不統一,尚未形成多數人認可、較為完善的評估標準,在生態資產分類、各種生態資產單位面積價值確定、不同生態資產價值重要性及權重確定、價值評估方法運用等諸多方面存在不同認識和分歧,因此生態資產價值評估結果差別較大,未能衡量出生態資產擁有量及價值總量。
家底不清不利于對生態資產進行科學認識和有效管理。此外,在生態資產的消耗和轉移方面也難以建立相應的生態補償機制,導致生態供給與經濟發展不平衡,從而又制約經濟增長。
《21世紀》:您是否對我國的生態欠賬做過估算?
高吉喜:如果按照當前趨勢發展,今后我國的生態欠賬將進一步擴大,據估算到2030年我國生態欠賬將達到6.5萬億元,到2050年將達到9.1萬億元,如果不改變現有的發展模式,可持續發展將面臨更為嚴峻的考驗。
建議組建生態資產核算框架
《21世紀》:就未來構建中國的生態資產管理和核算制度,您有哪些建議?
高吉喜:首先,應該設計一套完整的生態資產評估制度,可以由四個部分組成:生態資產統計、生態資產估價、生態資產賬戶平衡和生態資產報告。
同時,我們應該組建生態資產管理部門和賬戶,提升生態資產管理水平。
可以參照美國、挪威和法國的經驗,依托環保部門成立“生態資產核算委員會”,在中央層面率先建立生態資產技術支持機構,該機構負責研究制定及修正生態資產評估技術規范,建立人才培養和后續培訓機制,完善評估機構,加強生態資產監管。國家管理部門應加大對生態資產管理力度,參考聯合國和世界銀行記賬系統(SNA)和聯合國環境與經濟綜合記賬系統(SEEA),將生態資產納入經濟社會記賬系統。
同時,我們應以生態資產轉移為出發點,以資源、產品輸出地為補償主體,分析生態資產輸出主要影響因素,進而分析出補償重點,按照輸入量比例,輸入地對輸出地進行補償。針對生態資產跨境轉移存在的污染物滯留、內涵能源出口等問題,加強我國基于生態資產跨境轉移的生態補償機制研究。在生態補償框架約束下,優化進出口貿易結構,使對外貿易由主要依靠價格競爭、數量擴張及片面追求速度,轉向提高質量、效益和技術含量的方向,在減少中國貿易價值量順差的同時減少資源環境逆差,從而達到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