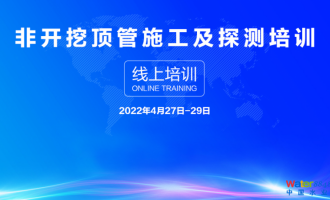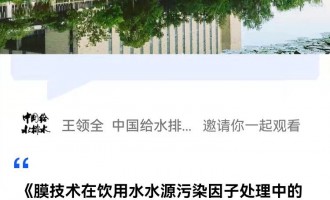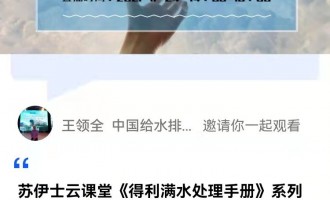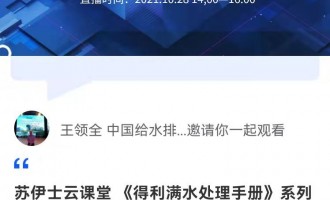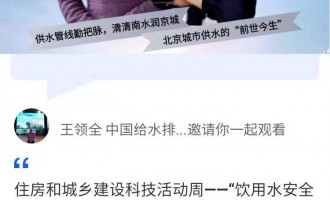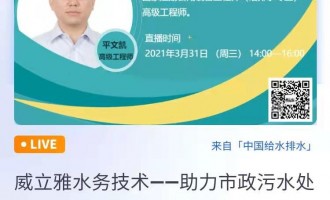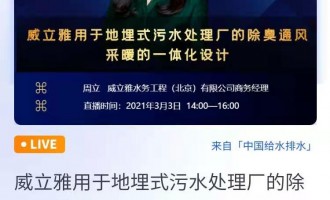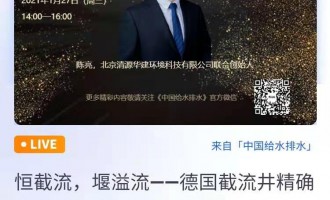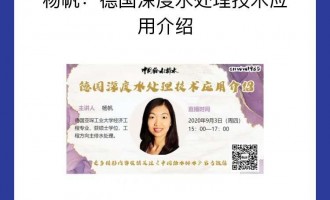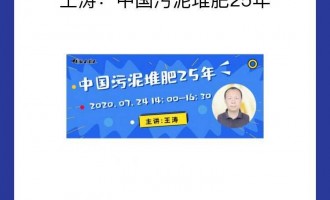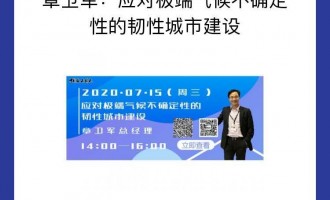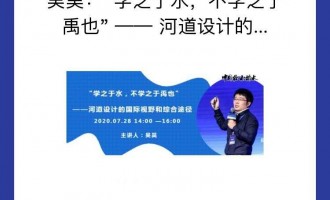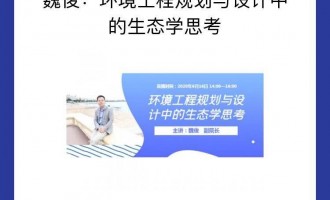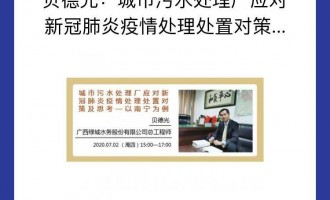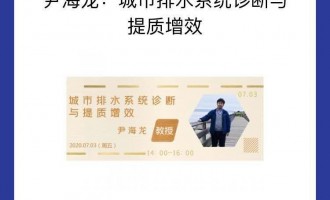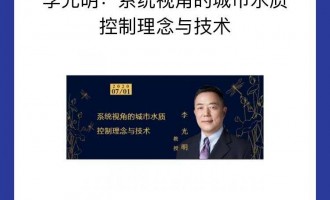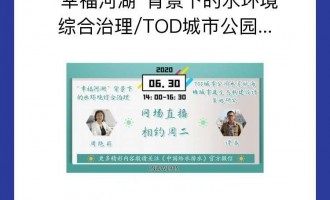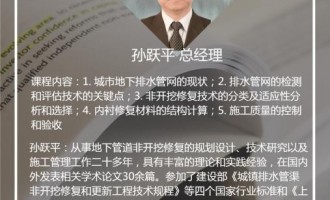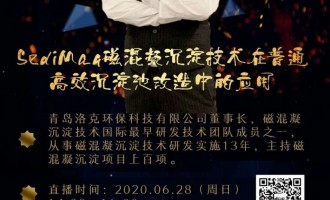環境治理事關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人民群眾的生存與健康,是一場持久戰,需要政府、企業和公眾的共同努力。借鑒發達國家污染治理歷程,環保企業有信心、有能力在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用10至20年的時間有效解決我國環境污染問題,為實現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建設美麗中國宏偉目標貢獻力量。——《環保企業家就當前環境時局致社會各界的倡議書》
“投資并運行著全國50%的城鎮污水處理設施、65%的垃圾焚燒設施、13%的電廠脫硫設施。”如今,專業化環保企業已經站在我國污染治理的一線。在他們眼中,環保不僅是安身立命之所在,也是一種使命。對環境保護目前面臨的新形勢、新問題,這些企業家有著表達觀點、參與推進環保進程的急迫意愿。
在今年全國政協會議開幕的當天上午,全國工商聯環境服務業商會(以下簡稱環境商會)組織環保企業家代表與“兩會”代表、委員座談。環境商會會長、北京桑德集團董事長文一波在會上宣讀《環保企業家就當前環境時局致社會各界的倡議書》(以下簡稱《倡議書》),提出了立法、監管、政策等多項建議。
怎么解決綜合性環境問題
“從中東部的霧霾揮之不去,到一些城市地下水污染嚴重,局部地區土壤污染程度加劇。回顧最近10年,各種污染事件層出不窮,污染類型、規模、環境損害等都日趨擴大,空氣告急,水源告急,土壤告急。我國環境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峻形勢。”文一波說。
對此,全國人大代表、中科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組長王毅表示,在討論環保下一步怎么做之前,首先得對當前的環境形勢做出基本判斷。“事實是,我國面臨的環境問題已經發生了轉型,從單一到復合,從點源到區域流域。大氣方面,區域性、復合型的污染問題不斷涌現,水的問題更多表現為流域性、復合型污染。”
“此前我們在點源控制、去除單一污染物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績,技術管理上都積累了不少經驗。但坦率地講,這些解決不了復合型污染問題。在新形勢面前,有必要對現行的相關法律、規劃、政策等進行適時研究和調整。”王毅表示,對中國現在的環境問題沒有靈丹妙藥,無法一招解決。
“只對一兩種污染物進行總量控制、削減是不夠的,對綜合性環境問題的解決需要一系列的控制指標和相關治理、保障措施。”王毅指出,比如對霧霾治理,就要對涉及其中的重要污染指標建立總量控制和削減時間表,而且必須要落實到區域。“以行政區劃分配減排目標,不能徹底解決問題。北京把工廠搬遷,可周邊燃煤污染同樣可以傳導過來。”
期待立法監管先行
在《倡議書》中,環保企業家首先呼吁應加快環境立法工作。當務之急是抓緊修訂《環境保護法》,以及大氣污染、水污染和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加快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制定并完善相關環境標準,完善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制度。同時,以法律形式保障公眾環境權益,擴大公眾參與范圍,提高公眾參與水平,加強環境信息的透明化、環境決策的民主化。
其次,加大環境監管執法力度。環境監管部門應加強組織能力建設,加大對專業機構、重點行業和重要污染源的監管執法力度。實行部門聯動,綜合利用財政、稅收、金融、限批等手段對環境違法行為予以懲戒。
為推動環保工作切實到位,企業家建議,國家應制定主要污染物減排時間表和重點區域流域達標時間表。力爭用10~20年時間,使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基本達到環境容量閾值,各重點區域流域環境質量實現達標。
對企業家的倡議,王毅表示,應對環境問題,國家層面應有一整套的系統設計。首先要立法,要有科學系統的規劃。他強調,不是單一而是區域性流域性的規劃。“法律法規、政策標準、規劃目標有了,然后才是環保技術、產業的問題。要確保法律、政策、規劃得到執行,監管到位,環保投資要落實。”王毅同時指出,針對環境問題進入高發期的形勢,除了有長期的政策規劃,還要有應急措施。“我們需要從過往的環境事故中吸取經驗,建立環境應急系統。比如針對霧霾,地方政府不能沒有應急措施。”
碳稅或可率先突破
“要加快出臺環境稅,本著先易后難、稅費并舉的原則,逐步設立和征收。建議目前開征SO2稅、NOX稅和工業COD稅3個稅種。”在倡議書中企業家的這一建議,得到了全國政協委員、財稅專家賈康的贊同。
他說,任何監管都要考慮成本,因此在承認監管必要性的同時,要找到低成本實現監管的合理路徑。“如果算上小微企業,全國現在有4000萬個市場主體,應該重視經濟杠桿形成的約束力和推動力,這也是一種監管。”
賈康解釋說,比如通過資源稅改革,讓基礎能源產品和其他各種產品的比價關系更加合理,讓生產、消費主體感覺到能源產品金貴,要精打細算,有內在動力去節約,這比派很多機構、人員去監管更能推動節能降耗。“政府在政策設計時,要注意讓大部分企業可以發展,讓真正落后的生產力、過剩的產能遭到淘汰。”
賈康說,政策層明確“十二五”要推行環境稅改革。這項工作要分為兩個部分。一是現有的稅種的綠化。比如燃油稅就是對成品油消費稅的一種改革,通過經濟杠桿、信號調整消費行為。二是推出獨立的環境稅種。比如碳稅。“針對某種污染物而對排放主體施加稅賦,難度很大,但我們認為這更值得看重并予以推行。”
在企業家提出的環境稅種中,碳稅可能會率先有所突破。“歐洲的基本經驗是掌握企業一年化石能源消費量,然后按照每噸化石能源形成的碳排放核算企業的碳排放量,以此為依據征收碳稅,這個框架較為簡單。價格可以從較低水平開始,5元~10元每噸,先建框架,讓各相關主體對新的機制有一個適應理解的過程。”
賈康說,誰排放得多,就承擔更多,這在經濟上是合理的,而且可以幫助生產主體約束排放行為,開發節能降耗的產品、工藝技術,這是推動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經濟手段。
“國際經驗表明,要把獨立的碳稅設計為一個雙重紅利的實現過程。一是把排放主體造成的外部負面效應、社會成本內部化,也就是環境成本內部化。二是如果要開征環境稅,就要降低企業所得稅稅賦水平,保持企業總體稅賦不變。
投入到底怎樣才有效率?
在《倡議書》中,企業家們提出了落實環保投入和強力推行治理設施專業化運營兩個建議,均屬于促進環境保護與環保產業良性互動的保障措施。
在投入方面,《倡議書》中建議未來10年要確保環保投入占GDP比重達到2%~3%,大致需投入10萬億元,其中各級財政需投入兩萬億元,以緩解現有環保投入不足問題。對此環境商會秘書長駱建華解釋說,“這是一個非常粗略的計算。還不一定夠。”
文一波也深以為然。他分析說,首先,我國環境欠賬多,霧霾、地下水、土壤污染等就是此前環境欠賬的集中暴發。其次,我國重化工比重大,污染更為嚴重。“如果想要遏制污染,改善環境質量,環境投入的比例還要逐步提高。”
文一波同時表示,投入方式的優化比數量的增長有時更為重要。“以前財政對環境基礎設施也花了不少錢,但是否發揮了應有的效果,要打個問號。”
文一波介紹說,以污水處理為例,財政資金絕大多數補貼給工程,而工程運營是否達到預期效果,沒有人關心。這就造成大家一窩蜂上項目,把一個小項目費力變成大項目去爭取財政資金,結果造成嚴重的浪費。
“如果財政投入的比例不變,那么方式應該變。應該從鼓勵建設轉向補貼運營效果或是減排成效。”他表示,要對切實削減了COD、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或是推動流域環境質量得到改善的企業或地方,采取補貼或獎勵。不但可以切實發揮財政資金的效果,也能催生持續、健康的產業市場。
對此,金州集團總裁蔣超深有體會。他說,現在很多經濟欠發達地區在財政支持下建設了污水處理廠,但沒錢運行,因為污水費收不上來。“難道欠發達地區的污染治理設施就要成為擺設?事實上很多欠發達地區在流域上游,污染得不到治理,會影響整個流域環境問題的解決。”
此前,環境商會和眾多環保企業家多年“上書”,建議成立全國性的環境基金,對污水處理設施運營進行補貼,專門支持達標規范的運營。
而推行治污設施專業化也是多年來業界呼吁的重點。從“誰污染誰治理”到“誰污染誰付費”,讓工業企業無法穩定達標運行的治污設施移交給專業環保企業,這其中當然有環保產業發展擴大市場的考慮,但從客觀上,治污專業化、市場化將帶來治污效率的顯著提升和環境監管壓力的紓解。
環境商會副秘書長馬輝表示,目前,工業企業大部分都還是自己負責廢水、廢渣、廢氣治理設施的運行。現行監管環境下,其運行效果無法保證,各種應付檢查、弄虛作假的案例屢見不鮮。即使出了事,處罰力度也缺乏足夠的震懾力。
“如果交給第三方專業的環保企業,那么每一個治污項目的運行效果不僅關系到能否拿到治理費用,而且事關運營企業自身聲譽,他們有關注運行的內生動力。一旦形成規模,一家環保企業可能會有十幾個、幾十個甚至上百個項目,從環保部門角度,關注一家環保運營企業,就可以管住眾多工業源。”馬輝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