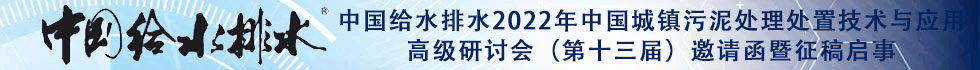蘇南地區,涵蓋南京、鎮江、常州、無錫、蘇州五市,以鄉鎮企業和開放型經濟引領發展之先。工業發展的同時,生態遭到破壞,甚至曾出現太湖“藍藻事件”。5年間,通過生態修復,蘇南恢復濕地10萬多畝,完成綜合治理、封育造林45.46萬畝,治理礦山宕口總面積達1374萬平方米。
“隨著發展步調的深入,蘇南人對全面發展的理解也越來越深刻。生態意識覺醒的蘇南人正重構著江南水鄉夢……”江蘇省委書記羅志軍如是說。
蘇南正恢復為“夢里水鄉”
在蘇州市吳江區正在建設的太湖新城,記者看到:岸邊橫臥一條深入湖面、寬敞漂亮的百米生態親水木道;岸上林木森森,姹紫嫣紅;湖面波光粼粼,水質清澈。新城的生態雛形初現……
2008年,吳江東太湖綜合整治工程啟動。通過退漁還湖、退墾還湖、生態清淤、生態治理和洪道疏浚五部分工程,太湖環境承載能力和區域防治能力得到全面提高。目前,退漁還湖及前期圍墾區動遷安置補償工作已基本完成,堤線調整和生態清淤工程正在實施。
“20萬畝的東太湖圍網,已縮減到4萬畝。180多億元建設資金,用于生態修復的就高達70億元。”吳江區委書記梁一波說,“太湖新城的未來就是人與自然更加和諧的生態城。”
“要治好太湖,先要治好蠡湖。”蠡湖治理辦公室原總工程師楊志毅說。2002年以來,在系統考察和學習國內外淡水湖泊治理經驗的基礎上,無錫按照“清淤、截污、調水、修復生態”的整治思路,全面實施生態清淤、污水截流、退漁還湖、湖岸整治等五大工程。積10年之功而終成,蠡湖獲得新生。數據顯示:曾經的劣V類蠡湖水,已連續兩年多穩定在類,水質達到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水平。
早在2005年,南京就開始治理廢棄宕口。8年來,南京投入3.26億元,治理89個宕口,治理總面積達708萬平方米,修復了開山采石造成的山體創傷。無錫、蘇州、鎮江等地也建立礦山生態環境恢復治理示范工程,采取造景、生態復綠等形式綜合治理。“蘇南正恢復成為山清水秀的‘夢里水鄉’。”江蘇省環保廳廳長陳蒙蒙說。
“修復環境,就是修復生產力”
“沒有宜居的環境,怎能算是人間天堂?沒有魚米之鄉,又怎能稱為福地江南?蘇州已到生態修復和環境再造的時候了!”江蘇省委常委、蘇州市委書記蔣宏坤的一句話,道出蘇州生態修復的原因。今年4月,蘇州正式出臺生態文明“十大工程”,包括東太湖綜合整治、土壤山體修復、陽澄湖生態優化等工程,總投資2000億元。
與東太湖地區一樣,蘇南在經濟發展的同時,環境問題日益嚴重。陳蒙蒙坦言,蘇南產業和人口高度集聚,城鎮化率超過70%,土地開發強度較高,生產空間布局不合理,生活空間不夠舒適,生態空間受到擠壓。“生態文明、環境保護是江蘇發展的一道坎,下一步,江蘇一定要邁過這道坎。蘇南一定要重視生態修復。”
如今,生態修復在蘇南各地正成為一種新氣象:蘇州繼為濕地保護立法后,今年再一次通過立法方式,確保百萬畝優質水稻、百萬畝特色水產、百萬畝高效園藝和百萬畝生態林地;無錫投巨資建起環太湖生態景觀林;南京關停并轉了300多家高污染、高消耗企業,并決定今后3年,不再批建增加煤炭用量的項目……
南京林業大學教授阮宏華說:“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修復環境,就是修復生產力。”
“生態文明絕不是不發展的文明”
生態文明是發展的必然選擇,但生態文明絕不是不發展的文明。既要發展經濟,又要保護生態環境,如何找準平衡點?
常州溧陽市委書記盛建良認為:“生態本身就是財富,兩者不矛盾。”溧陽市戴埠鎮李家園村通過生態修復、整治改善農村環境、挖掘利用山林景區資源優勢,在收獲綠水青山的同時也收獲著經濟發展。2012年,全村實現經濟總收入2億元,村級集體收入648萬元,村人均純收入2.5萬元。由于生態優越,當地產的茶葉要比其它地方的同品種茶葉貴一倍。
蘇州市吳中區委書記俞杏楠則認為:“要懂得生態與經濟之間的舍與得。”近10年,吳中區生態文明建設投入已超140億元,未來還將投入新增財力的10%到20%用于污染治理。吳中通過提高環保準入門檻,否決、勸阻、拒絕投資近20億元,依法關閉重污染企業50余家。但吳中探索出一條綠色發展之路:一方面,大力發展文化旅游業,做優做美太湖這篇文章;另一方面,實現農村股份合作社全覆蓋,成立14個集體經濟鎮級集團,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
對于無錫宜興市委書記王中蘇來說,“再生態化提供了轉型思路。”發展環保產業成為宜興的轉型之路。如今宜興的環保產業總量占全國的1/6、全省的1/2;水處理產業更是占據國內市場的“半壁江山”。
不久前公布的《蘇南現代化建設示范區實施意見》要求,“深入實施生態文明建設工程,建立經濟發達、人口稠密地區生態建設與環境保護新模式,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的生產生活方式,加快構建‘兩型社會’。”生態修復成為蘇南現代化建設新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