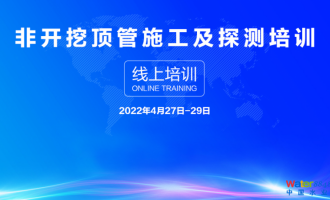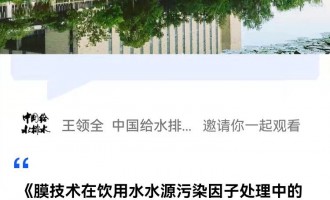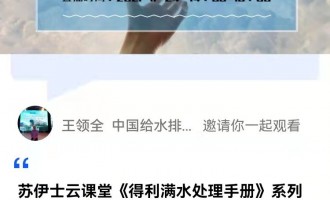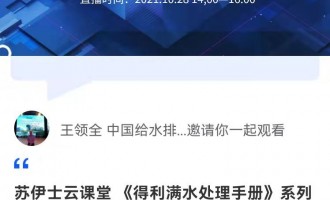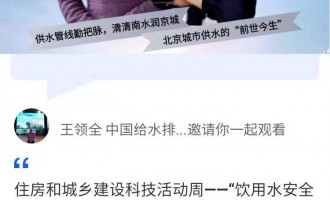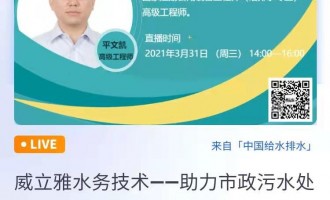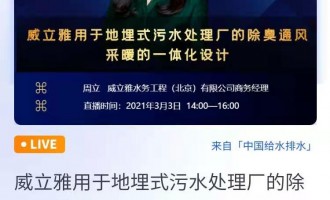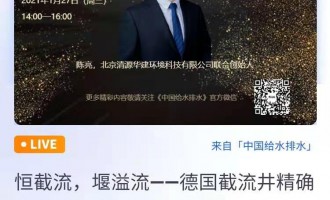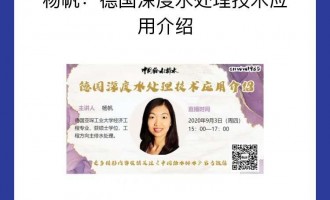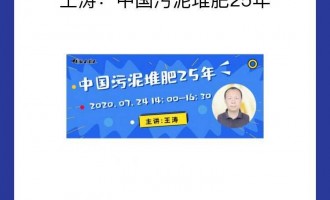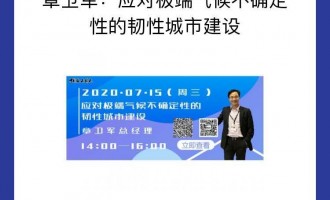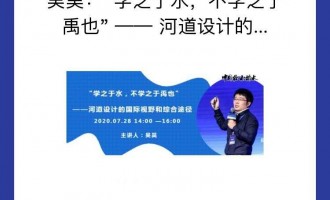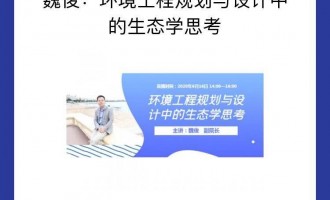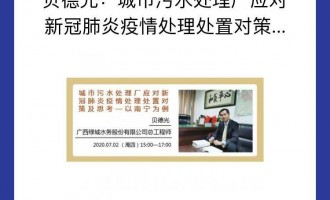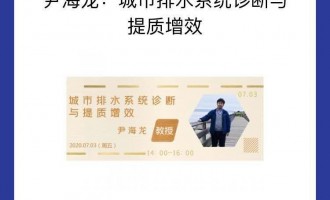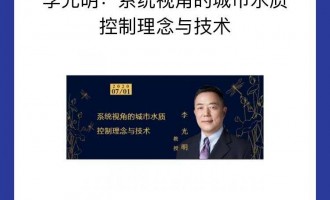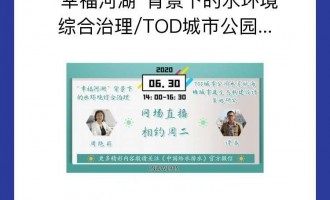法學界普遍認為,環境法是改革開放以來最早啟動和體系化的一部部門法。環境法的很多制度是國際借鑒和國內創新的產物,不可謂不先進,不可謂不實際,理應在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既解決嚴重的環境問題,也促進經濟和社會的良性發展。
事實證明,作用發揮了,但是在強大的經濟發展規模、宏大的經濟開發領域和快速的經濟發展速度面前,環境法的總體作用在過去30多年卻并不是那么理想。
水系和近海水質至今未得到根本改善,土壤污染威脅食品安全,大氣霧霾侵害國民健康,原因何在?
應從環境法治的立法、執法、司法、守法、法律參與和監督幾個環節去尋找答案。總的來看,既有環境立法的制度設定和條款設計問題,也有實施的問題。
1979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并頒布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1989年12月2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公布并施行。
共6章,包括總則、環境監督管理、保護和改善環境、防治環境污染和其他公害、法律責任和附則。
作用發揮緩慢
法律難以在短期內解決經濟長期增長帶來的環境問題
經濟本身的屬性是市場的,如果不加任何束縛,經濟的增長是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的增長。如果國家權力完全剝奪經濟發展的自由性,用計劃來替代市場,那么經濟的市場性就遭到扼殺,經濟就變成完全沒有自由度的計劃經濟。
基于這一點,可以說,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體制改革,不是我們創造市場活力,而是給市場松綁,廢除無所不在的管制式規則,使潛在的市場規則轉變為現實的市場規則,釋放市場本應有的活力。
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史是給經濟逐漸松綁,發揮其利潤,創造本性與活力的歷史。中國的經濟松綁改革是成功的。我國用短短的30余年,就走過了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的發展路程。
但是市場也是自私的,松綁后如不加以適當引導和法律限制,產生的負效應,如侵害他人和社會利益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也是驚人的。因此,需要給“野蠻”的市場附加必要的公法管制規則限制,使其發展規模、速度和方式理性化。
由于環境法律的實施涉及利益調整,難度很大,加上法治文化不足,要想短期內發揮大作用,很難。打個比方,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好比打開了上游的大壩,水會因為動力的長時間蓄積沿河流奔流而下,短時間就到達下游的目的地。而環境法律規則的遵守好比水由低處往高處流,如要到達上游的目的地,需要不斷的倒灌式積累,水位到達一定高度才行。
因此,想通過30多年的“應對式”環境立法,解決30多年經濟“傾瀉式”發展所帶來的環境問題,是幾乎不可能的。
2000年4月29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
共7章,包括總則,大氣污染防治的監督管理,防治燃煤產生的大氣污染,防治機動車船排放污染,防治廢氣、塵和惡臭污染,法律責任和附則。
法律規定滯后
歷史性環境債務越積越多,環境問題得不到有效遏制
由發現問題到制定法律規則需要一個過程,往往現實問題很嚴重了,才開始考慮立法問題,因此立法的預見性不足。
滯后性是世界各國立法的通病,只是滯后程度不同罷了。
法不能脫離現實的社會關系,否則就會成為“一疊不值錢的廢紙”。環境立法應該與我國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共進步,同發展,才能實現環境立法的最終目的。
在現實中,一些學者和媒體對可能出現的環境問題很敏感,披露具有預見性。
但是對現實問題的預見要得到立法采納,變成立法規范的預見性,往往需要立法機關的可行性論證。
而可行性論證往往受到各方面的力量左右。在很多情況下,環境立法新問題的預見性往往被利益集團的強大力量所埋葬。
即使立了法,法律規則的實施往往受到與利益集團有著千絲萬縷關系的執法者的選擇性或者漠視性對待,因此,環境法難以全部解決現行的環境問題,不可避免地留下歷史債務。
但是如果環境法律規則的設計適當,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歷史債務會得到后續的解決。
舊債沒有解決,快速的經濟增長還會不時催生新的環境體制和制度問題,又需要新的立法予以解決,這時又需要環境法的立改廢,而立法是有周期的,往往難以及時響應,就會產生新的問題。
新的問題和老的問題疊加,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就越難得到有效的遏制。
1989年3月,世界環境保護會議通過了《控制危險廢物越境轉移及其處置巴塞爾公約》,以防止危險廢物越境轉移對人類健康和生態環境造成災難性的危害。
我國參與了該公約的起草和通過,并于1991年9月4日批準加入該《公約》。1992年5月5日《公約》生效。
虛化條款過多
環境法的實在效應總體不高,難以發揮應有作用
環境法是環境法律規則的總稱。法律規則須是能夠發揮實在作用的準則,即能夠判斷行為是否合法以及如何評價并處理的準則。
為了配合這些準則發揮作用,環境立法除了闡述國家的政策和工作方針外,基本上都設置一些不帶法律后果的鼓勵性和限制性條款,如鼓勵干什么,支持干什么,引導干什么,限制干什么等,以營造法治氛圍。
這些條款,很多環境法學者也將它們納入法律規則的范疇。但是,這些條款的數量不能過多。
如果鼓勵性和限制性條款過多,從表面看來,涵蓋面好像更廣一些,但是由于缺乏法律后果的支撐,這些規定在實實在在的利益面前就難以發揮有效作用,形同虛設,這樣會淡化環境法姓“法”的特點。
從實踐來看,環境法的獎勵規定、促進科技發展的規定、促進公眾參與和監督的規定,就是如此。
如《循環經濟促進法》第7條:“國家鼓勵和支持開展循環經濟科學技術的研究、開發和推廣,鼓勵開展循環經濟宣傳、教育、科學知識普及和國際合作。”第10條:“國家鼓勵和引導公民使用節能、節水、節材和有利于保護環境的產品及再生產品,減少廢物的產生量和排放量。”
類似的虛化規定太多,不僅解決不了什么問題,還對樹立國家環境立法的威信不利,因此飽受環境法學界的詬病。
法律是解決問題的實在工具,虛化的條款設置過多是與法律的實在性原則相違背的,必須加以解決。
1999年12月25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修訂通過了新版《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環境保護法》。
共10章,包括海洋環境監督管理、防治陸源污染物對海洋環境的污染損害、防治海岸工程建設項目對海洋環境的污染損害等。
利益疏導不夠
違法成本低于守法成本,環境法應然作用的發揮打了折扣
法律是為了解決現實問題而制定的,法律的實施就是為了解決現實問題,從而調整某些方面的利益關系。
而我國現實的環境問題,是市場越軌帶來的利益問題。要破解利益問題,往往比觸及靈魂還難。
因此,總的來說,法律的實施具有被動遵守和消極抵制兩個特點。
由被動遵守到自覺遵守,由消極抵制到理性支持,既需要法律文化的培育,還需要法律的利益雙向調整,即對守法的利益支持和對違法的利益剝奪。
在環境法律體系的建設過程中,利益支持規則應當與利益剝奪規則的建設并重。但是,遺憾的是,前者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如果單純地通過管制的剝奪性方法來解決法律遵守問題,缺乏合情合理的利益支持機制,環境法律實施的阻力會越來越大。阻力越大,違法的幾率也越高。
一些地方缺乏系統的思維,無窮無盡地給企業施加各種雜亂的環境保護工作指令,包括一些缺乏法律依據的指令,這讓企業應接不暇。
企業即使努力地實現了,也心里打鼓,不知政府下一步又有什么大的動作,擔心自己能不能承受得起。
因此,守法成本太高,企業的抵觸心理越來越強。成本低的環境違法行為成為一些企業不得已的選擇。
一些地方為了促進本地的GDP,防止企業大量倒閉,也不愿意完全按照環境法律的規定辦事。基于此,舊的環境法律難以有效地解決長期存在的問題,新的環境法律也難以應對新出現的問題。
1995年8月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了《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暫行條例》,以加強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保護和改善水質,保障人體健康和人民生活、生產用水。
《條例》規定了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的目標,適用于淮河流域地表水體的污染防治。
監督機制缺乏
行政力量掌控過強,環境法的限權功能彰顯不足
法治社會應當是一個充滿監督的社會。
按照法理,社會公眾的監督及司法機關的監督設置缺位或者退位,行政權就會越位甚至替位;社會和市場的權利維護機制欠缺,行政權就會濫用、缺位或者不到位。
只有加強社會、市場參與和監督的渠道建設,建立有序參與、表達、申訴和監督的制度和機制,吸納他們共同參與國家事務,才能使公眾切實理解國家和社會建設的難處,提升國家的法治文化和氛圍,化不滿、不合作為積極的參與、合作。
從現實能力上看,環境保護需要常態化監管,而政府監管力量的存在與出現是偶然的,具有視野有限的不足。因此,對于環境違法行為,政府因為力量不足經常出現現場監管缺位的現象。
政府對所發現的違法行為作出處罰,相對廣泛的違法行為而言,具有個別性和偶然性的特點,不能全面、有效地打擊違法行為。而社會公眾監督資源非常豐富,在絕大多數場合,他們的發現與監督力量是常態存在的。
目前,我國的環境立法和法律實施,過分強調行政力量的掌控作用,公眾的常態性發現與監督力量不被重視,導致環境保護釣魚執法、選擇執法、尋租式執法、非文明執法、限制式執法、運動式執法、疲軟式執法、滯后式執法等執法不公、執法缺位的問題層出不窮。
這一問題使環境法律規范的實施走了調,變了樣,環境法應有的獨立功能也沒有得到有效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