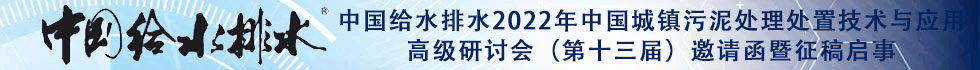來源:《環保產業》特刊
六部委與三部委: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
2005年10月,國家發改委等六部委聯合發布了《關于組織開展循環經濟試點(第一批)工作的通知》,標志著我國園區循環化改造工作的開端,當時被選入的產業園區共有13家,按照數量依次為華東4家,華北3家,西北和東北各2家,華中和西南各1家,華南零家(圖1)。2007年,又有20家產業園區被選入第二批循環經濟試點,這一次的對象以重化工集聚地為主,按照數量依次為華東6家,西北、華南和華中各3家,西南和東北各2家,華北1家(圖2)。至此,我國工業園區循環化改造的地理格局已經大致呈現。
2007年4月,國家環保總局、商務部和科技部聯合發布了《關于開展國家生態工業示范園區建設工作的通知》,標志著我國園區生態化改造工作的開端。次年即2008年5月,有3家園區成為第一批被正式授牌的國家生態工業示范園區,2011年12月,第二批12家被正式授牌,2012年7月又有2家通過驗收(表1)。因此迄今為止,我國名符其實的只有這十七家國家生態工業示范園區,其中華東地區占了五分之四強,特別是江蘇一省就占了將近半數(圖3)。
分別由六部委和三部委主導實施的園區循環化與生態化改造雖然走了不同的道路,但終點或者目標都是一致的,如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清潔生產與循環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喬琦所說,“都是為了讓發展更合理,綠色程度更高。”就好像生態與循環本身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樣。“可以說循環化改造有80%以上都是在國家生態園區建設的基礎上來申報的,而且這樣的效果比較好。如果原來一點基礎都沒有,在方案論證的時候就比較困難,畢竟理念好體,落實困難。這兩項工作是相輔相成的,第一批循環經濟試點的園區,基本上都是先創建生態工業園,之后在列入到發改委,包括環保部在內的六部委推薦。”喬琦說。
若一定要論區別,則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支持方式不同。循環化改造由以發改委為首的六部委負責,而生態化改造由以環保部為首的三部委負責,兩支領導力量本身的職能不同,所以給予支持的落腳點和具體形式也不盡相同。循環化改造的前方是真金白銀,利益顯性;而生態化改造的前方是績效光環,利益隱性。
第二,周期節奏不同。循環化改造是針對園區的配套基礎設施和關鍵補鏈項目建設給予一次性的打包支持,雖然中間有考核驗收甚至扣款規定,但是建成后不再跟進,因此代表的是一個終點;生態化改造以三年為周期對已命名園區進行評估,不合格者會被勒令限期整改,屆時仍達不到要求則會被除名,因此代表的是一個起點。
第三,改造對象不同。這個差別十分細微,即生態化改造的對象是工業園區,而循環化改造的對象是產業園區——除工業外,農業也被包含在內,如陜西省楊凌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示范區,但總體上還是向重化工等高耗能高污染的工業園區傾斜。
第一二代與第三代產業園區:長大后,我就成了你
繼20世紀70年代末經濟特區之后,我國又先后出現了兩類新型的開發區:經濟技術開發區和高新技術開發區,分別被稱為第一代和第二代產業園區(表1)。兩代園區起步期相差大約十年,但是發展的理論基礎、啟動背景和成長軌跡大同小異。而且近年來出現了結構趨同的現象:一方面知識經濟的大環境讓經濟技術開發區在發展現代工業的同時,也致力于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有些基礎較差的高新技術開發區本身的“高新”特征不很鮮明,特別是在國家推行“科技興貿”戰略的環境下,很多園區選擇了出口導向,致力于提高國際競爭力和出口創匯能力。
當前關于第一代和第二代產業園區的未來前景,一共有三種發展模式被提出,即并行發展,擇優發展和合一發展,各有針對性。它們恰好也分別體現了園區一次性創業(生存創業),二次創業(生態創業)和三次創業的需求。其中二次創業是兩袋產業園區共同面臨的現實問題,即按照生態原則和循環經濟理論重塑和改造一次創業——傳統產業園區——的成果,以謀求人類的可持續發展。這是循環化和生態化改造的需求動力和市場基礎,也是第三代產業園區,即生態工業園(Eco-Industrial Park)的誕生意義。
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傳統產業園區中各企業的生產過程相互獨立,這正是造成污染嚴重和資源消耗過多的中藥原因。生態工業園著力于園區內生態鏈和生態網的建設,仿照自然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方式,打造不同企業之間共享資源和互換副產品的產業共生關系,使上游生產的(伴生)廢物成為下游生產的原料,從源頭上將污染物排放量減至最低,實現區域清潔生產。目前世界上公認的最成功的生態工業園模式是丹麥的卡倫堡共生體系。
補鏈與靶向性招商: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卡倫堡也不是
從卡倫堡的共生模型來看,成就其今日的生態鏈總共花去了 50 年的時間,而且仍然有繼續增補的空間。其實在我國也一樣, 無論是生態化改造還是循環化改造,都少不了一個補鏈的過程。清華大學環境學院國家環境保護生態工業重點實驗室的石磊將補 鏈分為產業鏈補鏈,副產品交換補鏈,廢物處理補鏈和基礎設施補鏈這四種形式。這其中,產業鏈招商主要是以形成產業集群 (cluster)為目的,是最基本,最常見的補鏈行為,例如 IT 制造業集群和家電產業集群等,而生態化和循環化改造主要是通過其 他三種補鏈行為來實現。
基礎設施補鏈:基礎設施一共包含六個系統,其中有三個系統的內容都直接或者間接需要環保企業的參與,在園區外亦如是。 若從生態鏈條的角度出發,則這些基礎設施不能再像從前一樣扮演單一的承上或者啟下的角色,而是要融入到閉環模式中,其中 最常見的就是水資源的循環再利用——這也是國家生態工業示范園區的重要指標之一。然而,即便是已經為環保企業駕輕就熟的 這些業務,放在園區中也需要重新考慮選址分布和管網輸送等內容,在照顧到全區規劃的同時,盡量做到低影響開發。
廢物(副產品)交換補鏈:除了工業企業之間的生態鏈條外,還有很重要的一環是靜脈產業的參與,這種交換關系主要是讓環保企業來發揮變廢為寶的功能。而反向來說,類似于海水淡化這樣的戰略 性節能環保項目所產生的廢物也可以為工業所用。例如 2007 年就曾有專家隊伍為總設計規模 140 萬噸/日的曹妃甸海水淡化項 目做了濃鹽水利用的可行性研究,包括計劃讓兩家鹽場接收濃鹽水來制鹽。只是筆者在將近三年的追蹤中,始終看不到實質性進展, 再三追問下才得知,除海水淡化項目本身的問題外,循環鏈條中各相關方由于分屬不同的管理部門,而且存在輸送障礙,所以推 行困難。如今世異時移,2011 年曹妃甸新區與唐山三友集團合作開建濃海水綜合利用項目,據稱雙方在實現淡化海水和濃鹽水交 換后,可節省原鹽 60 萬噸/年和水資源 1000 萬立方米/年,大大降低了海水淡化和鹽化工的生產成本。另外,濃鹽水還可以用 來提溴和其他具有高附加值的產品,也為很多工業園區所看重。
簡單來說,卡倫堡模式的成功正是在于不斷通過副產品交換補鏈,廢物處理補鏈和基礎設施補鏈而完成一幅漂亮的拼圖。世界上除了卡倫堡之外,還有五種生態工業園區模式比較有代表性。
有了對比,才會知道差距。關于我國如何在實踐中做好生態化和循環化改造的工作,順利實現園區和環保企業的供需對接, 中持水務總經理朱向東給出了四個要點。不難看出,前兩點主要落在園區身上,后兩點主要落在環保產業身上。
政策法規和標準指南:讀你們千遍,也不能厭倦
有關園區生態化和循環化改造的工作指令始于2005年,之后又有所跟進、補充、修訂和強化,從而形成了現有的法規標準體系。單從文件發布的時間密度上就可以看出國家對于這兩類工作的重視程度,發改委和環保部(原國家環保總局)為此做出的努力有目共睹。再加上近期剛剛發布的《“十二五”節能環保產業發展規劃》《廢物資源化科技工程“十二五”專項規劃》和即將正式發布的《環境服務業“十二五”發展規劃》《全國循環經濟發展總體規劃》等有關政策預期,我國的產業園區已經加速駛入綠色轉型的上升通道。
2012年8月,環保部對2009版的《綜合類生態工業園區標準》進行了修改,刪除了指標中“工業增加值年均增長率”和“中水回用率”兩項及相應的指標值要求,同時在生態工業園區的基本條件中增加了第八條“園區經濟保持持續增長, 且國內生產總值三年年均增長率不低于所在地級及以上城市國內生 產總值三年年均增長率”和第九條“園區應積極開展再生水利用,再生水利用應符合當地有關政策和標準要求”。 這兩項指標的放松應該可以讓為此撓頭的園區管理者深感欣慰,也說明生態化改 造的標準體系正在追求理想化目標的同時,兼顧實際可行性。然而,也不排除很多園區依然會自我嚴格要求。環保部科技標準司 副司長劉志全表示:“某些園區已經到了自我鞭策的程度,其節能減排指標遠遠高出了國家要求。”
雖然《行業類生態工業園區指標》和《靜脈產業類生態工業園區指標》還在試行,但是這些指標的設定已經能夠讓很多環保企業對號入座,為有需求的園區量身定做產品和服務。特別是有關“園區管理”中對信息平臺完善度的要求,更加說明環境服務的重要性。這個領域需要越來越多有綜合服務能力的企業提供包括設計、工程、融資、咨詢、公關等在內的全方位服務,這一點不單在生態化改造的指標上有所體現,循環化改造的主要任務也無一不在傳遞著這樣的信息——在空間布局合理化,產業結構最優化,產業鏈接循環化,資源利用高效化,污染治理集中化,基礎設施綠色化和運行管理規范化這七項任務中,后五項都為環保企業提供了市場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