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郭媛媛 于寶源 環境保護 2022-08-01 15:10 發表于北京
收錄于合集#院士說12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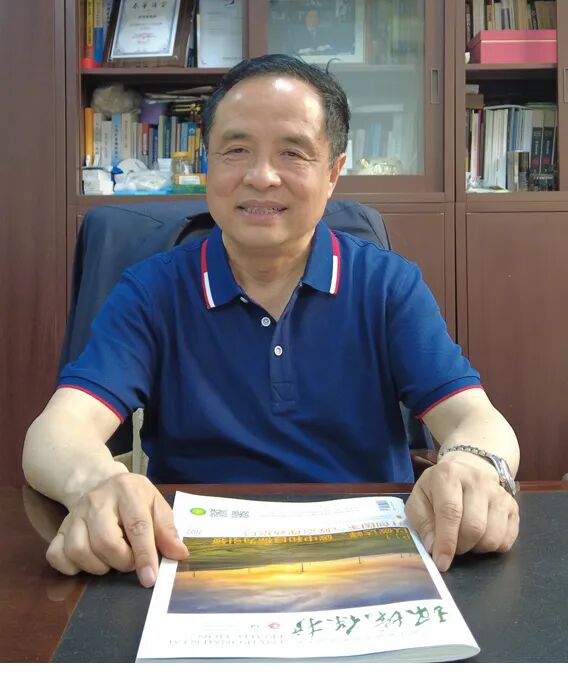
彭蘇萍,2007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礦山工程地質與工程物探專家,能源環境專家。于1988年在中國礦業大學北京研究生部博士研究生畢業,獲煤田地質與勘探專業博士學位。現任中國礦業大學(北京)教授、煤炭資源與安全開采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彭蘇萍院士研究發現煤層砂巖頂板變薄尖滅帶是頂板災害易發區,建立了煤層頂板穩定性地質預測技術與方法。率先開展了煤礦三維三分量地震勘探技術研究,建立了以野外采集評價技術、三維地震可視化解釋與反演技術、縱橫波聯合解釋技術為基礎的煤礦高分辨三維地震勘探技術體系,并將物探技術與水資源保護利用相結合,促進生態修復在煤炭企業廣泛推廣應用并形成不同的修復模式。研發了固體氧化物燃料電池儲能調峰技術方法,對于煤炭綠色轉型和生態修復協同碳中和,具有較好的推廣應用潛力。先后榮獲了國家科技獎5項,省部級科技進步特等獎1項、一等獎4項、二等獎4項(均排名第一),軍隊科技進步二等獎1項(排名第二);取得了國家軟件版權6項、發明專利27項,出版專著11本。
2021年9月22日印發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指出,要以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為引領,加快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能源體系,嚴格控制化石能源消費,加快煤炭減量步伐,“十四五”時期嚴控煤炭消費增長。2021年11月2日印發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意見》指出,要以減污降碳協同增效為總抓手,切實維護生態環境安全,持續提升生態系統質量,科學推進歷史遺留礦山生態修復,開展大規模國土綠化行動。未來,我國傳統能源與新能源之間會是怎樣的一種關系?煤炭綠色低碳轉型的路徑是什么?煤礦塌陷區實施生態修復的意義和重要性體現在哪些方面?會產生怎樣的生態效益、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近日,《環境保護》雜志記者對中國工程院院士、煤炭資源與安全開采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中國礦業大學(北京)礦山生態修復研究院院長彭蘇萍進行了專訪,請他談一談對上述問題的思考與實踐。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實現離不開煤炭綠色轉型的積極貢獻《環境保護》:我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以下簡稱“‘雙碳’目標”),煤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彭蘇萍:我國擁有全球最大的能源系統,也是最大的煤炭生產國和消費國。2020年,我國煤炭相關產業二氧化碳排放量約76億t,占我國二氧化碳總排放量的77%左右。大規模開發利用的煤炭是我國最為突出的溫室氣體排放源。能源行業是我國實現“雙碳”目標的關鍵。從我國能源消費結構看,化石能源占84%的比重,其中,煤炭占57%,天然氣和石油占比為27%;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只占到16%的比重,其中,水電占7%,核電占3%,其他6%為風電、光伏、生物質和地熱能。我國一年消費石油約7億t,但是自產石油只有2億t,其余5億t石油則依賴進口。在一定時期內,煤炭仍然是我國能源安全的基石,煤炭綠色轉型是實現“雙碳”目標的必然選擇。《環境保護》:煤炭等化石能源綠色低碳轉型路徑是什么?化石能源與新能源將以怎樣的關系并存? 彭蘇萍:世界各國能源綠色低碳轉型的路徑與方式各有不同,這是由各國資源稟賦與技術優勢差異所決定的。從世界能源格局和資源稟賦看,我國實現“雙碳”目標比歐美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難度都要大一些。這是因為歐洲主要依賴天然氣,美國主要依賴石油,我國則主要依賴煤炭,而煤炭是化石能源中碳排放最高的。此外,歐洲除天然氣外,還有核電做支撐。而我國受地理環境和地質構造等因素影響,有些地區建設核電站難度很大。碳約束將深刻影響和改變我國現有能源開發利用方式。我國應立足國情推進綠色轉型。煤炭綠色低碳化發展是我國實現“雙碳”目標的關鍵。推動經濟增長模式的綠色低碳轉型不可能一蹴而就。當前一個時期內,我國還是要實行“兩條腿”走路。一是通過技術創新將高碳能源低碳化利用。化石能源在使用過程中會排放大量二氧化碳,給減排造成巨大壓力。實現煤炭低碳發展,須依靠顛覆性技術創新。我國多煤少氣,需要發展煤氣化技術,尤其需要發展二氧化碳近零排放的煤氣化燃料電池發電技術。整體煤氣化燃料電池可以突破以往燃煤電廠通過汽輪機發電的模式,提高煤氣化燃料電池發電效率,降低二氧化碳捕集成本,同時實現二氧化碳及污染物近零排放,是煤炭發電的根本性變革技術。以燃煤電廠為例,采用煤氣化燃料電池發電技術可以直接把在發電過程中產生的二氧化碳進行富集處置,使其不排到空氣中,同時將發電效率從30%提升到60%,這樣可以減少一半的煤炭使用量。高碳能源低碳化利用方面的技術創新工作還需要我們不懈努力。煤炭低碳發展助力碳達峰的措施還有:大力發展煤炭開采碳排放控制技術;降低煤炭開發利用的能源消耗強度;提升用煤質量,減少煤炭利用碳排放;推動煤炭向原料、燃料并重轉變;推動煤炭與其他能源實現融合發展;研發實用的碳捕集、利用與封存技術。我們對煤炭技術比較熟悉,因此,我國的煤炭低碳化利用問題不是很難解決,只要在政策上支持,在資金上引導,在科學上重視,一定會取得重大突破。二是通過技術創新提升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比例。實際上,我國一直非常重視能源轉型,期待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得到大幅度提升,但是這個難度相當大。我國的風電和光伏發電產業主要分布在西部,距離東部經濟發達地區較遠,造成了空間上的障礙,需要發展大規模儲能調峰技術。這也是目前氫能與燃料電池技術快速發展的原因。氫能產業鏈長,涉及制氫、儲運氫以及以燃料電池為代表的應用技術。目前國際上應用最為廣泛的燃料電池有固體氧化物燃料電池和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技術。固體氧化物燃料電池發電,或通過燃料電池的逆過程電解水制氫,以及電解二氧化碳制一氧化碳,可以使風能、太陽能等高效轉化成可持續能源,是未來有前景的能源轉化儲存和碳中和技術。與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90℃左右的工作溫度相比,固體氧化物燃料電池工作溫度可以高達700℃左右,一次發電效率可以達到60%,比較適合大規模供電與集成式發電。除了發電效率高外,固體氧化物燃料電池發電技術的余熱品質也很高,溫度可高達600℃,可以用于熱電聯供,熱電聯供效率可達到90%以上。可以說,基于固體燃料電池的分布式發電是十分高效、環保的燃氣發電技術。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對氫氣的質量要求高,因此其成本較高。目前,煤制氫過程中的氫氣純度還達不到質子膜燃料電池的要求,還要進一步分離提純,因此社會上廣泛提出了“綠氫”問題。實際上,問題不在氫上,主要還是燃料電池的問題。質子膜燃料電池的工作溫度太低,如果采用工作溫度高的固體氧化物燃料電池,就不存在這個問題。固體氧化物燃料電池不要求純度很高的氫氣,而且除氫氣之外,還可以用天然氣、石油氣、煤的合成氣等替代氫氣作為燃料,其供給模式可以不打破現有能源供應鏈。固體氧化物燃料電池技術還有一個優勢,其待機啟動所需時間在半小時以內,非常適用于電力調峰。“雙碳”目標的提出對我國來說是一個機遇。在今后的20~30年,我國要繼續拓展應用可再生能源,必須要解決調峰問題。對于分布式固體氧化物電解池制氫,我們計劃在山東建設若干個示范基地,并利用集裝箱的堆疊解決氫的儲運難題,節省儲運成本。另外,我們也希望將固體氧化物燃料電池技術應用到居民小區里,作為小區供熱或制冷的來源。固體氧化物燃料電池高效發電和固體氧化物電解池分布制氫技術的發展對于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比例具有很重要的作用。通過固體氧化物燃料電池技術實現化石能源利用的“零碳”排放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可以說,未來10~20年將是我國氫能源產業發展的重要機遇期,我國需緊密聯系能源發展實際,助力實現氫能源高質量發展,從戰略、政策、技術、資金、國際合作等多方面積極謀劃,通過改革創新破解發展難題。《環境保護》:大力推動技術創新是實現煤炭綠色低碳發展的利器,這對煤炭開采和煤炭生產企業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人們的普遍印象中,煤炭開采的負效應是帶來生態環境的破壞和惡化。您認為我國煤礦區的生態環境保護和修復工程如何制定和實施將更有助于“雙碳”目標的實現?彭蘇萍:西北地區是我國主要的煤炭基地。我們的課題組曾經對這一地區的生態環境進行了20多年的長期監測。監測結果表明,從1990年西部煤炭規模化開采以來,西北地區的生態環境不是逐漸變差,而是逐漸變好。這徹底改變了煤炭開采只會破壞生態環境這一傳統觀念。大自然原本就具備自我修復的功能和潛力。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文明觀是我們需要遵循的。人工生態修復與自然生態修復共同促進了礦區生態環境的正向演替。其實,煤炭開采與生態環境保護并不矛盾,通過技術手段可以實現協調統一的雙贏目的。比如,煤炭開采會使地面沉陷并出現裂隙。以前相關方面的專家都只關注到這是對自然生態的一種破壞,造成漏水、漏肥、拉傷根系。其實產生的裂隙也可以是一種有效的生態修復方式,就像農民在耕種前先要松土一樣。通過裂縫的松土作用,提高土壤入滲能力,增加土壤透氣性,輔以適量生物土壤改良技術,可促進農作物的增產、增收。可見,煤炭開采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具有正負兩方面效應,開采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用“損傷”描述比“破壞”更為貼切,這是我們從幾十年的工作成果中得到的一個結論。比如,晉陜蒙黃土高原在20世紀80年代種植了很多樹木,但是直到如今樹木仍只有幾米高,生長緩慢;而通過生態修復后的煤礦區種植的樹木就能夠長到十余米高,整個礦區的生物多樣性也明顯增多。通過與周圍生態環境的對比,發現其主要原因是煤礦區生態修復或重建時,將表土環境整個給“刨”或“翻”了一遍,打破了原有的生態環境和不利于植物生長的環境因子,促進現有生態環境的改善。我國部分地區由于無限制地獲取自然資源,沒有對區域資源枯竭后轉型升級進行長遠規劃和布局,造成區域經濟衰退。我們不能再走這些地區的老路。課題組對煤礦區的生態環境保護和修復工作進行了認真思考,提出了“三個區域富饒”生態戰略構想,即煤礦開采奠定了區域富饒,煤炭開發實現了區域富饒,生態修復延續了區域富饒。以內蒙古鄂爾多斯和陜西榆林兩個以煤、煤化工為基礎的工業化城市為例,我們通過“全周期生態演變四維監測、生態安全影響程度評價及預測、地下水保護與礦井水處理、沙塵智能監測與沙塵綜合防控、生態減損開采、生物種群優化配置、鹽堿地微生物修復、土壤修復與植被恢復”八項核心技術,將煤礦區變成了一個景色優美、生態宜人的宜居區。《環境保護》:我國煤礦區的生態修復該如何進一步拓展思路,發揮積極作用? 彭蘇萍:我們的長期跟蹤研究顯示,開采之后的煤礦塌陷區通過生態修復治理可以變成固碳的新場所。修復后的土壤本身能夠固碳,種植的草木也可以吸收二氧化碳。我們算了一筆賬,如果把全國所有煤礦塌陷區80%的面積進行生態修復,至少能固碳11億t,若是降雨量再加大一點,還可以增加10%的固碳量。所以煤礦開采煤炭之后,積極探索“以‘主動治理’替代‘被動修復’,以‘全過程治理’替代‘末端治理’,以‘邊開采邊治理’替代‘先開采后治理’,以‘開發同時保護’替代‘先開發后保護’,以‘煤礦區產業高質量發展’促進‘地區社會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的煤礦生態環境修復新模式極其重要。煤礦區的生態修復是我國實現碳中和不可或缺的中堅力量。通過反哺政策進行生態修復,使得挖煤后的礦區生態環境比開采前好很多。30年前進行大規模煤炭開發的內蒙古鄂爾多斯和陜西榆林地區,以前大部分地區都是沙漠地帶,現在則變成了一片綠洲,就是最好的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