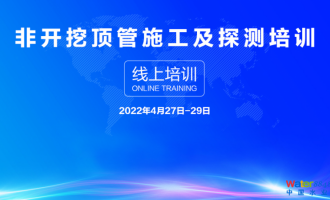WATER8848前言:針對中央督察組發布的青海省海北州礦山生態環境綜合整治不徹底、治理修復問題突出的典型案例,可以看出企業主體責任的喪失和相關部門監管“寬松軟”是問題的主要原因。
首先,企業作為礦山開采的主體,應該承擔起環境保護和生態修復的責任。如果企業缺乏環保意識,不履行主體責任,就會導致礦山生態環境遭受破壞,治理和修復工作難以推進。因此,需要加強企業的環保意識和責任教育,建立健全企業主體責任制,對不履行主體責任的企業進行嚴厲處罰。
其次,相關部門監管“寬松軟”也是導致礦山生態環境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的重要原因之一。監管部門應該加強對礦山開采和生態修復的監管力度,建立完善的監管機制,對違法違規行為進行嚴肅處理。同時,也需要加強對企業的日常監管和巡查,及時發現和解決問題。
最后,需要強調的是,礦山生態環境治理和修復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企業和政府共同努力。政府應該加大對礦山生態環境治理和修復的投入,加強政策引導和支持,鼓勵企業積極參與生態修復工作。同時,也需要加強社會監督,讓公眾了解礦山生態環境問題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共同推動礦山生態環境治理和修復工作取得實效。
10余年7份方案,卻“填”不滿祁連山南麓的8個礦坑 | 中央督察典型案例追蹤
時間:2024-01-05 來源:中國環境APP 作者:中環報記者肖琪
8個毗連的露天采坑,邊坡是大量棄渣,山體有多處瘡疤,坑口總面積達117萬平方米。眼前觸目驚心的景象,位于祁連山南麓青海省西海煤炭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西海煤炭)所屬的柴達爾礦和柴達爾先鋒礦。
中央第五生態環境保護督察組近日發布青海省海北州礦山生態環境綜合整治不徹底,治理修復問題突出的典型案例,揭示了海北州一些地方在礦山生態環境綜合整治中,歷史遺留采坑、渣山治理不到位,部門監管存在“寬松軟”問題。
企業主體責任的喪失和相關部門監管“寬松軟”,讓一座座礦山歷經10余年仍得不到有效治理和修復,大地的瘡疤如此醒目卻痼疾難除。

2023年11月29日,督察組現場督察使用無人機拍攝,柴達爾礦采坑沒有完成環境整治工作
僅一路之隔,未修復的礦坑近在眼前卻視而不見
2020年祁連山南麓木里礦區非法采煤事件的曝光,將祁連山地區非法開采,嚴重破壞生態環境的真相公之于眾。打著生態修復治理的名義非法采煤,興青公司給當地政治生態和自然生態所造成的破壞觸目驚心。
中央第五生態環境保護督察組在青海省督察期間,以青海省《木里礦區(江倉一號井)暨祁連山南麓青海片區生態環境綜合政治方案》下達的798個“疑似圖斑”為線索,重點前往祁連山地區查看礦山治理與修復情況。
目標很快被鎖定。在一份《海北州剛察縣采礦權綜合整治匯總表》中,督察人員發現了一條重要線索:2020年,當木里礦區工礦企業全面關停之際,剛察縣境內與798個“疑似圖斑”有關的大部分企業都停產或退出,但卻有一家例外——青海省西海煤炭開發有限責任公司所屬的柴達爾礦和柴達爾先鋒礦仍正常生產。柴達爾礦直至2021年8月受“8.14”重大潰泥潰沙事故影響,才與柴達爾先鋒礦一起停產整頓至今。
為何別人都停,它不停?按照相關政策應開展的生態修復治理工作效果又會如何?督察人員帶著疑問出發了。
在企業工作人員的帶領下,督察人員來到柴達爾礦和柴達爾先鋒礦已經停產的礦區。12月的高原十分寒冷,大風吹得人睜不開眼。
“這一處修復得還不錯,回填后也種了草。”正當督察組成員以為此行會無功而返時,往前走了幾步,立刻發現一路之隔的北面,有一個巨大的礦坑出現在視野中。
如此掩耳盜鈴般的修復只是個例嗎?
順著這一思路深挖,督察組最終發現,柴達爾礦、柴達爾先鋒礦兩個礦區長期開采形成了8個相互毗連的露天采坑,邊坡堆放大量棄渣,山體留下多處瘡疤。截至督察進駐時,采坑應回填土石方量6694萬立方米,實際只回填了865萬立方米;16座渣山共計12600畝需要治理,僅完成7470畝,治理工作嚴重滯后。

2023年9月9日,督察組暗查發現,衛星圖片顯示柴達爾礦、柴達爾先鋒礦長期開采形成8個相互毗連的露天采坑
7份方案“填”不滿8個礦坑
典型案例指出,2009年至2020年,海北州和剛察縣兩級政府和企業先后制定各類治理整改方案共7份,都提出要限期完成采坑回填、渣山治理、地貌植被恢復等整治工作。
10余年過去,方案出了一份又一份,但礦坑治理卻長期只停留在紙面上中,難以落實、落地。直至此次督察進駐,礦坑仍未回填,更遑論開展后續治理工作。
看著眼前并未完成生態修復的巨大礦坑,手中拿著礦坑修復通過驗收并整改銷號的文件。督察人員坦言:“這根本說不過去。”
根據剛察縣人民政府提供的《關于剛察縣八個礦坑恢復治理情況的說明》, 實際上,早在2017年第一輪中央環保督察時,督察組就曾反饋過海北州114宗礦山(含柴達爾礦和柴達爾先鋒礦中的8個礦坑)未能按時限要求及時完成治理任務。
剛察縣從2017年起,督促西海煤炭依據相關規定,對照渣山治理、采坑回填、環境整治、地表覆土、種草復綠等5個目標,按照“高削低填、銜接順暢、過渡自然”的原則,加快工作進度。
企業也并非不治理,截至2019年,企業共完成回填平整面積865.35萬立方米、邊坡整治6.8萬立方米、覆綠277萬平方米。但8個礦坑的回填面積與應回填土石方量還是相差了6倍之多。根據剛察縣政府提供的材料,2021年煤礦停業整頓導致收入銳減,對恢復治理的投入不足,才導致恢復治理工作緩慢。
督察人員在相關治理方案中還發現一個數據,8個礦坑要完全治理好預計需花費7億資金。難度大、見效慢,一直是礦坑治理采坑回填推進困難的癥結所在。諸多因素混雜,加上如此大的修復資金和漫長的時間成本,讓破壞式開采給生態和經濟帶來的重創還在持續。
7道驗收關口層層失守,對礦坑避而不談也能整改銷號
2019年12月,海北州、剛察縣兩級政府對8個礦坑的治理完成驗收。這是當地有關部門最先開始對治理效果給予官方認定。
但就在州縣兩級驗收后的第二年——2020年8月,祁連山南麓木里礦區非法采煤事件爆發。隨即,青海省啟動木里礦區以及祁連山南麓青海片區生態環境綜合整治三年行動。青海省自然資源廳聯合多部門,對祁連山南麓青海片區的兩市兩州10個縣涉及生態環保的礦山企業、建設項目和礦業權等數量、位置、合法性和生態環境狀況等進行全面排查。此次排查共確定798個“疑似圖斑” ,其中就包括此次典型案例提及的柴達爾礦的4個礦坑(7號圖斑)和柴達爾先鋒礦的4個礦坑(8號圖斑)。
從2017年至今,歷經第一輪中央環保督察、祁連山南麓木里礦區綜合整治、青海省級生態環境保護例行督察,每一次都在傳導壓力,都指出了問題所在。但8個礦坑的治理始終提不上日程。
即便被納入祁連山南麓青海片區798個“疑似圖斑”整治范圍,剛察縣在2021年4月上報給青海省自然資源廳備案的治理方案中,也僅涉及部分渣山治理,對8個露天采坑避而不談。
這樣的治理方案不僅通過了,最終還變成了后續驗收的依據。
典型案例指出,柴達爾礦和柴達爾先鋒礦在整治任務未完成、整治目標未達到的情況下,順利通過了自查、縣級初驗、州級驗收、交叉檢查組檢查評估、省級考核驗收、專家組總體驗收和第三方評估等7道關口,并于2022年12月通過銷號,層層把關卻層層失守。
“我們思想認識不到位,以為前面(第一輪督察整改)已完成了整治,故未采取措施開展新的整治(798個“疑似圖斑”的整改工作)。”文件中這樣寫道。然而在8個毗連的露天采坑面前,這一解釋尤顯蒼白無力。
海北州對生態文明建設認識不到位,推進礦產資源生態環境綜合整治不嚴不實,省和州縣有關部門把關不嚴、督促指導不力,才是相關問題長期存在的深層次原因。
翻閱資料,很多地方都曾出現過“開一處礦山、毀一片草原、損一方生態”的現象。這背后依舊是經濟賬和生態賬的命題。社會的發展和進步離不開對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但如何處理好保護與開發的關系,是人類的永恒命題。
對于青海而言,最大的價值在生態,最大的責任在生態,最大的潛力也在生態。為了一時的利益破壞最大的生態價值得不償失。青海省這一最大的省情不會變,重要的生態地位更不會變,生態保護對于全省乃至全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這片72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最終將開出怎樣的生態文明之花?當地黨委、政府及有關部門重任在肩,使命如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