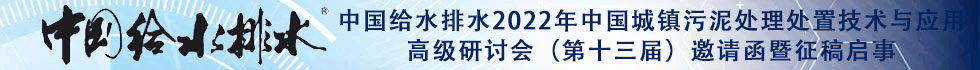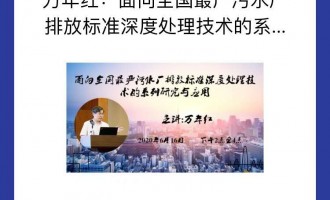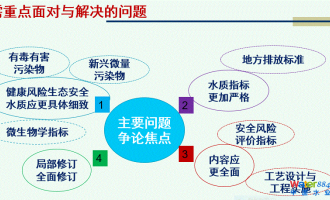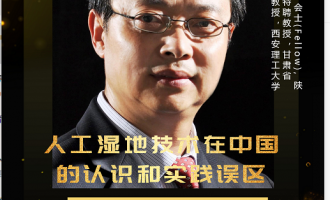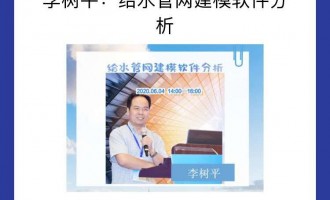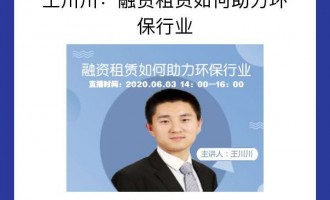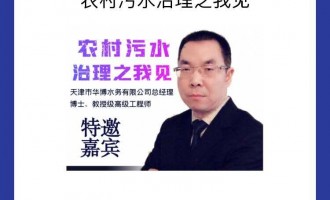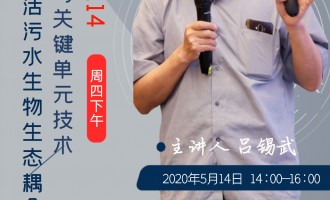“如今大家只看到土壤修復市場這塊肥肉,卻沒看到未來的風險和責任。”
一座密閉車間矗立在一個化工廠原址上,卡車將挖出來的土壤運到車間內,大型攪動器翻動土壤,強制有害污染物揮發。揮發物被收集后,或被活性炭吸附,或被焚燒。
“類似的土壤修復的新技術正逐漸被應用。”北京建工環境修復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北京建工)技術總監馬駿說。
但更為原始的方法仍占中國土壤修復技術的主流,即把受污染的土壤挖出來,運到另一個地方進行填埋或焚燒。更多新技術難以被應用,修復企業也處于初級而混亂的狀態。
“有的先有工程,后有修復公司,就是有關系的人專門成立一家公司承接這個工程,所以它既缺設備也缺技術。”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副所長廖曉勇說。
“但土壤修復不是隨便可以糊弄的,將來是要追責的。”高勝達警告,“如今大家只看到土壤修復市場這塊肥肉,卻沒看到未來的風險和責任。”

工人正在鉆孔取土樣,設置地下水監測井。這是用注射修復藥劑的方法來“清毒”,這樣的新技術在全國應用并不廣泛。 (資料圖片)
“貧瘠土地”難開技術之花
異地填埋或焚燒,已開始被歐美國家拋棄了,但在中國仍是主流。
曾在美國留學、工作多年的馬駿介紹,美國、日本、歐洲曾以異地填埋或焚燒為主,但現在更多采用化學、生物領域的新技術,因為越來越嚴格的尾氣排放標準導致焚燒成本高企。
而中國又因為很多城市缺乏規范的填埋場,所以采用更多的是水泥窯焚燒。水泥窯焚燒會產生二噁英等劇毒廢氣。而馬駿稱,國內水泥窯一般不具備處置廢氣的裝置,因此產生的二次污染甚至比原污染物更為嚴重。
新技術難以被應用。北京市環科院副院長姜林透露,目前全國研發的土壤修復新技術約有一二十種,但都沒有得到市場應用。
原因在于,很多新技術的處置周期都比較長,而在房地產火爆的今天,土地流轉很快,開發商根本等不及調查和修復。即使修復,業主對周期也有嚴格要求,一般為幾個月到一年。
北京建工于2007年成立,是國內第一家以“土壤修復”作為主業的環境公司,其承接的所有修復工程中,被要求的處置周期沒有超過兩年的。所以只能通過異地填埋和焚燒的方式快速處理。
即使某些新技術被采用,開發商仍對處置周期要求“嚴格”。修復公司只好將土壤運到別處,不影響原址的工程開發進度。
開發商還要求修復價格低廉,這也限制了新技術應用。一位要求匿名的專家舉例說,2011年11月份,他參加蘇州市首例由政府財政支付修復資金的地塊招標評標活動。在這次招標方案的設置中,技術值只占40%,商務值占60%,所謂商務值就包含修復價格等因素。“我們(評標專家)都認為招標方案中,技術值應該占80%才科學。否則你技術值雖低,但只要綜合評分第一,就能拿到工程。結果必然是誰的價格最低誰中標。”他說。
誰污染,誰沒錢治理
目前,中國的土壤修復費用大多由政府直接承擔,或者在土地轉讓時折價。
北京建工至今修復項目至少十二個,費用支付的主體幾乎都是政府。盡管相關政策規定“誰污染誰治理”,但在中國很難執行。
“這些搬遷、破產的大多是國有、集體企業,若追責還是追到國家的頭上;有的地塊甚至轉手了好幾道,責任鑒定十分困難;有的已經破產,已無支付能力。”中國環境修復網執行主編高勝達說。
馬駿也稱,搬遷企業往往是落后產能,經濟效益原本就不好;另外,他們本不愿搬遷,更無動力支付昂貴的修復費用。
埋單自然落到政府頭上。然而,地方政府的積極性顯然不高。廣州市原南方鋼鐵廠保障房項目的土壤修復過程,頗能體現地方政府的微妙心態。
該場地第一次環評時,有16萬立方米的污染土壤,但審議時未獲通過。廣東省生態環境與土壤研究所研究員萬洪富曾參與了第一次環評審議,他當時建議補充加密調查重金屬污染和有機物含量。因為,鋼鐵廠一般都存在有機物污染。而施工方最終只做了重金屬污染調查。萬因此拒絕了第二次環評。他的觀點得到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教授劉俐的認同。
“之后,施工方通過我們研究所,要求我不要再提有機物污染的問題了。”萬說,“因為修復有機物污染,費用肯定要多。”
但這樣的環評報告卻通過廣州市環保局審批。環評結果顯示,重金屬微量超標的土壤僅為300立方米。
萬分析,南方鋼廠第二次環評之所以能夠通過,可能因為廣州市保障辦要在上級部門規定的時間內完成今年新建保障房任務,也是為了減少政府在修復費用方面的支出。但這或許給南方鋼廠保障房留下一些隱患。
淘金之地,無治之地
“以前參加行業會議的人很少,現在每次都是幾百人,每次都能發現新企業。”中國科學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員陳夢舫如此感慨。
投資者們都將希望寄托于未來的市場。種種跡象表明,土壤修復將是一個爆炸性行業。尤令業界振奮的是:2011年8月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通過了《全國地下水污染防治規劃(2011-2020年)》。
“在國外,土壤修復和地下水修復本就密不可分。而中國近5年來,都只是修復土壤,不修復地下水。被污染的地下水還會繼續污染土壤。”馬駿說。北京建工僅兩三例同時做了地下水修復。
重視土壤修復的城市正在增多。
北京市為了踐行“綠色奧運”的承諾,自2007年起,大規模啟動棕地修復工程。因世博會部分場館就建于棕地之上,上海也開展棕地修復工作。2011年6月,上海市環保局要求城市污染場地必經修復后才可再利用。
2011年6月,南京市也要求所有正在開發的項目必須開展環境風險評估,之前未經調查和風險評估的在建工程,必須停建,補充風險評估。這讓開發商們一時手足無措。
更令業界稱贊的是2011年12月1日,北京市正式實施《場地土壤環境風險評價篩選值》。它規定了住宅用地、工商業用地等不同土地利用類型下土壤污染物的環境風險評價篩選值,所涵蓋的污染物指標達89項。
在全國土壤修復行業缺乏法規、標準的背景下,這一國內首例地方標準,或對其他地區具參考價值。
就在土壤修復市場逐漸熱鬧喧囂之時,中國環境科學協會土壤地下水環境委員會副主任謝輝發出一個清醒的聲音:中國工業化發展較晚,應該吸取西方國家的教訓,積極預防土壤和地下水污染,“一旦進入修復,費用則十分高昂”。
“毒地”淘金
發自:北京 廣州 重慶 最后更新:2012-03-19
- 標簽
- 土壤修復
- 棕色地塊
- 土壤污染
- 環保
缺了技術,少了資金,“清毒”難上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