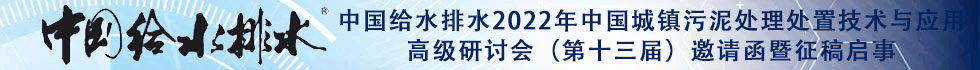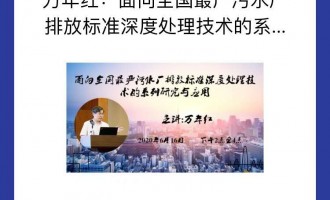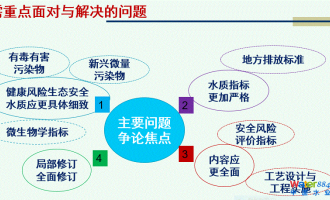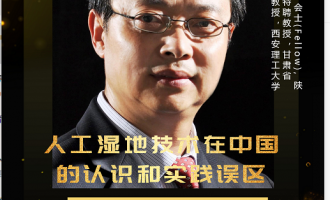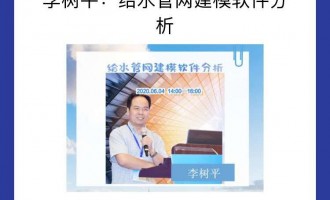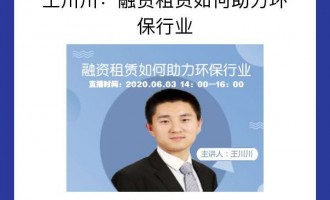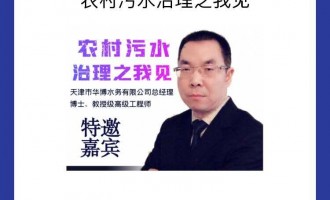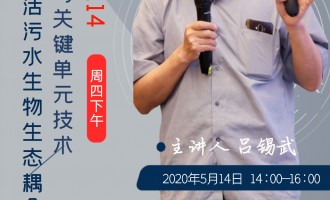20世紀60年代以來,環境問題日益凸顯,環境保護、環境治理等觀念越來越多的受到各界的關注與重視,環境保護基本法的積極作用也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所認可,不少國家相繼制定了環境基本法。例如,日本于1967年制定《公害對策基本法》并于1993年修改為《環境基本法》,美國于1969年制定《國家環境政策法》。中國的環境保護法較美國、日本相比制定較晚,我國1979年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1989年修訂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以下簡稱《環保法》),2014年4月24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八次會議對現行的《環保法》進行了修訂,新修訂的《環保法》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本次修訂對《環保法》做了重大修改,如將保護環境上升至國家基本國策;確定了新的環境保護機制,如信息公開、公益訴訟等。《環保法》的修訂標志著中國的環境保護法律體系步入了新的階段,環境保護行為已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然而,由于歷史背景及經濟體制等原因,我國的《環保法》與西方國家相比存在著共性與個性的共存,在此背景下,本文對美國、日本的環境保護發展史、環境保護法律體系、公民權利、罰款力度等進行了比較,在此基礎上,憧憬著中國環境保護的未來。
一、西方工業化國家的環境事件推動了中國環境保護工作的開展
美國、日本對環境保護意識的覺醒均來自于環境污染事件的頻發,正是由于西方工業化國家環境公害事件的頻發,推動了中國環境保護工作的開展,喚醒了中國環境保護意識的覺醒。
由于環境污染事件頻發,美國于1899年頒布了《河流與港口法》(亦稱《垃圾法》),這是美國頒布的第一個關于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隨后又頒布了《聯邦殺蟲劑法》,《防止河流油污染法》等法律。1969年,俄亥俄州的凱艾哈格河因嚴重化學污染引起河面著火的事件,引起公眾的廣泛關注,他們要求在聯邦層次上制定法律來保護自己的生存環境,在這種背景下,環境保護意見被徹底激發,《國家環境政策法》由此誕生。
日本環境問題的重視由“四大公害”事件引發。日本環境污染問題雖早有記載,但致使其大肆爆發的罪魁禍首是其50年代中期,提出的以產值、利潤為中心的全面推進“經濟高速成長”的發展戰略。在這一戰略的帶領下,全國上下至環境于不顧,大力發展工業,以經濟增長為目標,忽視各種污染物的排放量以及環境載體的破壞。直到70年代初,四大公害事件的相繼發生,(四大公害事件為:由有機汞而導致的水污染從而引發的兩起水俁病;由硫氧化物導致的大氣污染從而引發的哮喘;由鎘造成的水質污染從而引發的痛痛病),環境問題才引起了日本政府的重視。1967年制定了《公害對策基本法》,1970年,日本政府對該法進行了重大修改,刪除了“與經濟調和”的規定,正式提出了“環境優先”的原則,1993年將《公害對策基本法》修改為《環境基本法》,從而確定了其基本法的地位。
20世紀60年代末,由于西方國家環境公害事件頻發,聯合國決定召開第一次環境會議,中國被邀參會,正是通過這次會議,喚醒了中國人民對環境問題的重視,中國的環境保護意識開始覺醒。但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是,美國、日本等先進的工業化國家的環境保護工作從地方興起、在發展初期主要靠地方政府推動,而我國由于經濟體制的限制,重要決策的制訂與實施主要依賴于中央政府,環境保護行為的開展高度依賴于中央政府的推動。
二、《環保法》的環境地位已有顯著提升
新《環保法》采用了“基本法模式”,較之前《環保法》相比,該法的環境地位已有了顯著的提升,但不足之處是未將該法與其他法律的關系進行明確表述,或產生執法沖突。
美國《國家環境政策法》規定:“國家的各項政策、法律以及公法解釋與執行均應當與本法的規定相一致”,由此確立了其在環境保護領域的基本法地位。該法主要內容有4個方面:一是宣布國家環境政策和國家環境保護目標;二是明確國家環境政策的法律地位;三是規定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四是設立國家環境委員會。四方面的內容緊密相連,構成一個有機整體,這些規定也使其在美國環境法律體系中奠定了其基礎性地位。
我國新修訂的《環保法》提升了其環境地位。本法第一條指出,該法立法目的為:“為保護和改善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眾健康,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制定本法。”這體現了經濟發展凌駕于環境保護之上的時代已經過去。該法第四條中,將原《環保法》的“使環境保護工作同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相協調”,改為“使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相協調”,這也宣布GDP的增長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經濟發展應在環境保護的大框架下進行。
值得肯定的是,新《環保法》采用的是“基本法模式”,但與美國的《國家環境政策法》不同之處在于,未明確其基本法地位,未體現該法與其他法律的關系。我國環境保護方面的法律有20多部,就目前情況而言,部分法律相對于《環保法》仍有沖突的地方,例如環保法規定“罰無上限”,但在《水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中卻有著罰款上限的規定,明確其基本法地位或更有利于環境保護立法的實施。
三、公益訴訟主體擴大
新《環保法》擴大了有權提起公益訴訟組織的范圍,并明確了公民對環境信息獲取、參與和監督環境保護的權利。
在美國環境執法體系中,民間環保組織的力量不可小視,《國家環境政策法》賦予了公民對行政機關活動的環境影響進行評論的權利,《清潔空氣法》甚至專門規定了公民訴訟司法審查等條款,這些為公民執行提供了法律依據,當政府或企業違反環境法時,民間環保組織有權對其提起訴訟,《國家環境政策法》也明確指出了公民對于環境的權利,其第4331條規定,“國會認為,每個人都可以享受健康的環境,同時每個人也有責任參與環境的改善與保護”。
新《環保法》對公眾環境保護的參與問題有了極高的重視。新《環保法》明確規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依法享有獲取環境信息、參與和監督環境保護的權利”“重點排污單位應當如實向社會公開其主要污染物的名稱、排放方式、排放濃度和總量、超標排放情況”“公眾發現污染環境和破壞生態行為的,有權舉報”。如同美國相關法律一樣,新環保法擴大了能夠提起公益訴訟的社會組織的范圍,符合規定的社會組織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人民法院均應當依法受理,且未來有權提起公益訴訟的社會組織還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
但遺憾的是,本法只明確了公民有依法享有獲取環境信息的權利,對信息公開的時間、公開的形式沒有明確規定,目前,我國執法大部分依靠單行法,該部分內容或可在單行法中予以體現。
四、明確的職責分工是環境保護法落地執行的有效保障
界限明確的職責分工是環境保護法有效執行的保障,我國新修訂的《環保法》對責任分配方面有了突破性的進展。
日本的《環境基本法》對各方職責做出了明確規定,在該法的第6、7、8、9條明確指出:國家擁有制定和實施有關環境保護的基本的且綜合性的政策和措施的職責;地方公共團體擁有制定和實施符合國家有關環境保護政策,以及其他適應本地方公共團體區域自然社會條件的政策和措施的職責;企(事)業者有責任在進行其企業活動時,采取必要的措施,處理伴隨此種企(事)業活動而產生的煙塵、污水、廢棄物以及防止其他公害,并且要妥善保護自然環境;國民應當努力降低伴隨其日常生活對環境的負荷,以便防止環境污染,除前款規定的職責外,國民還應當根據基本理念,有責任在自身努力保護環境的同時,協助國家或者地方公共團體實施有關環境保護的政策和措施。
新《環保法》對政府、排污企業、治污企業及公眾的責任均做出了相關規定。該法明確規定:國家應建立跨行政區域的聯合防治協調機制;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對本行政區域內的環境質量負責;企業事業單位應執行國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標準,并盡量減少污染物的排放,在污染物總量指標不達標情況下,排污企業還要通過提高排放標準等手段來分擔政府壓力;公眾有義務保護環境、有權利監督排污治污企事業單位、有權利訴訟。
新《環保法》已構建了一個以責任為導向的法律體系,但具體的責任方面可參照西方國家較完善的環境保護法進行細化,亦可在配套法或單行法中予以體現,例如可參照日本的《環境基本法》將國民的義務進行細化,以便《環保法》在公眾群里中得到更有效的應用。
五、《環保法》提高了企業的違法成本
罰款被公認為在環境執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且一直以來用作處置環境違法行為的重要武器。罰款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威懾違法者,確保受管制者受到公平、一致的對待。
美國環境違法行為罰款力度之大已眾所周知。美國《清潔空氣法》(USC第7413節)規定,聯邦環保局長可以對違法行為人違法的每一天,處以最高2.5萬美元的罰款,處罰時效不超過12個月。美國《清潔水法》(USC第1319節)規定,如果某個環境違法行為處于繼續狀態,罰款就實行按日計算,每天不超過1萬美元;又如《環境責任法》規定對違法該法關于報告、保存資料、合作治理等條款的違法者,每次罰款2.5萬美元以下,每一持續日2.5萬美元以下,對累犯者,每一位持續日的罰款額可以達到7.5萬美元;《有毒物質控制法》規定,對于違法者處以每違法日2.5萬美元的行政罰款。
在執法方面,日本采取了“直罰主義”。日本的環境法律、法規設定了企業單位和國民的義務及具體排放標準,企事業單位的廢氣乃至排放的廢水中的污染物質若超出排放標準,執法機關則以違反行政上的義務為依據直接給以刑事處罰。若故意實施超標排放行為,可以對直接責任者或者企事業單位處以6個月以下的拘役或10萬元以下的罰金;過失超標準排出的,對其責任者直接處以3個月以下的拘役或5萬日元以下罰金。這種對違反排放標準的責任者可以不經過法院審判由執法機關依據環境法律、法規直接處以刑罰。
在環境執法中,我國對罰款的威懾性也十分認可。1989年頒布《環保法》中對罰款金額就有著明確規定,但其力度較小,環保部門對其最多罰款10萬元,并且每月只能罰款1次,這樣一來,即便每月都罰,一年也不過120萬元,企業違法成本較低,甚至出現了治污成本高于違法成本的現象,致使企業知法犯法。
而新《環保法》提出的對違規企業實施“按日連續處罰”及“雙罰制”,顯然加大了處罰力度,提高了企業的違法成本,但新的問題也隨之而來,罰款數額界定、罰款事項的透明度等或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環保法》是一個綜合性的法律,起引導作用,在配套法或單行法中可對違法行為的責任追究、處罰機制依據新《環保法》進行修改。
我國環境保護較美國、日本相比起步較晚,當前,我國環境保護法律制度建設所面臨的形勢在某些方面同美國在1960年所面臨的形勢十分相似,且日本的環境治理經驗:環境立法、民間維權、技術研發,可值得我國借鑒。但在歷史經驗借鑒的過程中,應注意到中國與美國及日本的基本國情、環境現狀、維權模式均存在差異,經驗的吸取與采納應與我國的實際情況相匹配,以確保《環保法》的有效落地執行,使環境得到更好的保護及治理。
中美日環境保護法“共性”與“個性”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