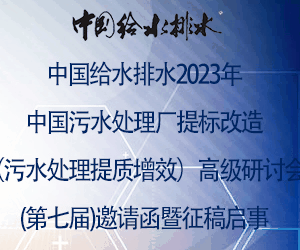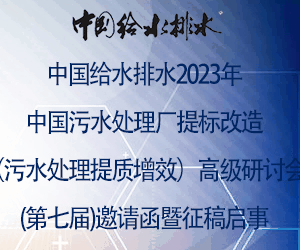“河長+檢察長”制度創新與實踐探索
時間:2020-09-18
來源:檢察日報
●“河長+檢察長”這種協作機制嘗試通過納入檢察機關的司法作用,來進一步提升“河長制”在河湖系統保護和水生態環境持續改善方面的效用發揮。
●目前,“河長+檢察長”的治理模式已在全國范圍內獲得廣泛推廣,拓寬了檢察公益訴訟的案件來源,提升了檢察監督的效能。
●跨區域司法大數據共享、分析和應用機制尚未有效建立,如何協調生態環境資源損害行為地和結果發生地的辦案訴求差異等,都成為亟須解決的問題。
伴隨公共治理的深化,對環境利益的維護在我國被予以突出強調。傳統高耗能、高污染和高排放的經濟發展模式,一味追求GDP增長的公共治理路徑以及生態環境系統自身的高度復雜,都成為掣肘環境治理迅速、有效推行的因素。也是在此背景下,“河長制”被作為地方環境治理的創新模式獲得廣泛推廣。
“河長制”最初因太湖藍藻事件而在江蘇發端,后被作為有益經驗而在全國推廣。這種制度的要點在于: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設立總河長,由黨委或政府主要負責人擔任;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行政區域內主要河湖設立河長,由省級負責人擔任;各河湖所在市、縣、鄉均分級分段設立河長,由同級負責人擔任。各級河長負責組織領導相應河湖的管理和保護工作。尤其是河流治理的規劃編制、督促和落實人員、項目以及資金的到位。“河長制”之所以取得顯著效果的原因在于:其一,它將環境治理尤其是河流治理的目標和責任細致落實到了地區行政首長身上,既確保了環境治理的權威性,也使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等生態文明建設指標被切實納入各級政府工作的考核評價體系;其二,它有效促成了河流水域的協同共治,這種協同共治不僅含括不同地區,也含括不同部門之間的聯動。因為省級政府首長作為總河長,而不同級別的政府首長和涉水各部門負責人擔任不同層級的“河長”,地區和部門沖突通過聯席會議予以協調和解決,由此也促成了水環境跨流域跨部門的協同治理;其三,它還創新性地引入了地方在環境治理上的“黨政同責”機制,即黨委主要領導同樣需作為河長承擔生態治理責任。
“河長制”獲得廣泛推廣后,在此基礎上又衍生出“河長+檢察長”的升級版協作機制。與此前的“河長制”相比,這種協作機制嘗試通過納入檢察機關的司法作用,來進一步提升“河長制”在河湖系統保護和水生態環境持續改善方面的效用發揮。而其基礎又是借助檢察公益訴訟制度。在各級河長辦公室與檢察機關聯合印發的有關協作機制如何展開的指導性意見中,協同領導、信息共享、辦案協作、聯合工作、日常聯絡等工作方式被作為協作機制的具體展開形式漸漸形塑出來。所謂協同領導,即各級河長與檢察長對水域治理的重點工作和重點案件,通過聯合巡查、聯席會議等方式進行協同領導、統籌規劃;而信息共享和辦案協作則強調雙方在案件線索、巡查結果和整改反饋等方面都應互相溝通、雙向移送;聯合工作、日常聯絡也旨在確保這種協同機制能夠有效發揮作用。
目前,“河長+檢察長”的治理模式已在全國范圍內獲得廣泛推廣,被認為拓寬了檢察公益訴訟的案件來源,且提升了檢察監督的效能。生態環境公益訴訟一直以來都是檢察機關強化行政公益訴訟的重點范疇。行政訴訟法第25條的規定也同樣意味著檢察機關在生態環境保護方面所應承擔的積極職責,它與檢察機關對于生態環境資源刑事犯罪的追究以及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一起,成為檢察機關在生態環境方面所應承擔的積極司法保障職能。
與其他的檢察公益訴訟相比,建立“河長+檢察長”制度之后的環境檢察公益訴訟表現出如下特點和優勢:其一,它將檢察行政公益訴訟的前置程序與恢復性司法理念在生態環境保護領域予以有效整合。檢察公益訴訟的前置程序意味著,當檢察機關發現行政機關“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作為,致使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應當向行政機關提出檢察建議,督促其依法履行職責。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行職責的,人民檢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此項前置程序設置的原因主要在于在檢察行政公益訴訟被提起之前,為行政機關提供再次履職的機會,由此保障程序經濟和節約司法資源。但在環境公益訴訟中,前置程序的運用本質上還有盡早完成環境修復,避免污染擴大的考慮。這一點也是“恢復性司法理念和實踐”在近期的檢察公益訴訟工作中被予以特別強調的背景,而“河長+檢察長”的有效聯動、協作辦案也被證明,能夠有效破解生態環境保護領域恢復性司法的難題;其二,生態環境治理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國家機關上下一體推動。“河長制”所調動的主要是行政資源和行政系統,此外還主要通過“黨政同責”將各級黨組織納入生態環境的治理體系。“河長+檢察長”制度則在此基礎上納入了司法系統,強化了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的司法責任與司法保護,由此也使生態環境的國家綜合治理體系更加完備;其三,這種創新性制度的出現也同樣推進了檢察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具體塑成與細化。我國的檢察行政公益訴訟確立時間尚短,制度也僅是初具端倪,因此需結合各個領域的具體實踐進行形塑和磨礪。而“河長+檢察長”制度的實踐恰好為生態環境檢察公益訴訟的制度塑成提供了場域和基礎。在推行這種協作制的過程中,最高檢曾出臺《關于長江經濟帶檢察機關辦理長江流域生態環境資源案件加強協作配合的意見》,明確跨省案件統一管轄和線索移送等五個方面20條具體措施。為解決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領域案件鑒定難、費用高的問題,最高檢還增加環境資源領域專業鑒定機構,推出檢察公益訴訟中不預收鑒定費的鑒定機構。此外,各地檢察機關還堅持以問題為導向,通過“建立臺賬、拉條掛賬、整改銷號”等獨具特色的制度,形成符合本地方特點的環境治理手段,并推進生態環境資源問題的集中治理。而在檢察系統內部,同樣針對環境污染問題的擴散性特點而進行跨省域的檢察協作與檢察保護,例如重慶、四川、云南、貴州四省市檢察機關共建的赤水河、烏江流域跨區域的生態環境保護檢察協作機制。上述制度創新都為我國檢察行政公益訴訟的持續推進和制度提升提供基礎。
但任何制度創新都會遭遇實施困難,也需要在化解與克服困難時再反復進行制度整飭與調試。從目前既有的“河長+檢察長”制度的實踐來看,這一制度的有效運作同樣遭遇如下問題:其一,行政與司法的協作尚未在檢察行政公益訴訟的制度框架下具體形成。盡管“河長+檢察長”制度的核心在于行政與司法的協作機制,但目前實踐中的這種協作只是通過聯合巡查、聯席會議等工作聯絡方面展開,并未形成有利于環境檢察公益訴訟有效開展的具體制度。也因此制度化水平不夠,行政與司法的協作就常常出現協作不深入、信息共享不及時、聯動辦案不緊密等問題,也常常流于協作的形式;其二,在檢察系統內部,檢察行政公益訴訟被作為生態檢察工作的重要一環予以強調,檢察系統也著力于促成以刑事檢察、公益訴訟檢察為主導,民事檢察、行政檢察為補充的基本格局,但刑事檢察與公益訴訟檢察如何有效銜接,尤其是與行政公益訴訟如何銜接,目前同樣未達成制度性共識和統一處理方式;其三,無論是“河長制”還是“河長+檢察長”制度,都根據環境治理的跨區域特點,著眼于建立跨區域的協作機制。但相比行政系統內部的跨區域協作,跨區域檢察辦案卻遭遇很多制度性障礙。例如,跨區域司法大數據共享、分析和應用機制尚未有效建立,對跨省市環境犯罪和違法的空間分布和轉移態勢進行細致分析、聯合發布數據分析報告,形成共管共治等機制尚不健全,跨省的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由哪個檢察機關具體提起,如何協調生態環境資源損害行為地和結果發生地的辦案訴求差異等,都成為亟須解決的問題;其四,完整的檢察行政公益訴訟不可缺失的一環是由法院來對檢察機關提起的檢察行政公益訴訟進行審查,但目前的“河長+檢察長”制度因為重點在于塑成行政與檢察的協作,因此在制度設計上未充分考慮法院的司法審判體制,這就導致某些創新性制度,例如跨流域的生態環境保護檢察機制與法院對于環境類案件的集中管轄之間相互抵牾,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跨流域生態環境保護協作機制所欲追求的整體化和系統性目標。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河長+檢察長”制度的創新雖然在實踐中帶來積極成效,卻也需要不斷進行實踐磨礪和制度調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