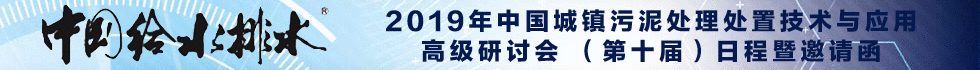黨的十八大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到國家戰略高度,提出要深入推進行政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環保體制和職能也面臨改革,筆者認為,當前急需厘清以下重要關系,為下一階段的轉型發展明確方向。
重新審視環境與發展關系
如何處理好環境與發展的關系是一個關鍵問題。在我國,政績考核是決定官員行動方向的指揮棒。長期以來,由于奉行片面重視GDP的政績觀,使得很多地方政府只重視經濟效益,客觀上加劇了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中組部前段時間印發了《關于改進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政績考核工作的通知》,明確了政績考核的新導向。但是,中央政策到了地方可能會出現矯枉過正的現象。
隨著政績考核方向的調整,當前更要防止兩種傾向:第一種是借產業結構調整的大旗,罔顧經濟發展規律,簡單地采取關、停、搬等手段加速傳統產業衰敗;或者,不愿承擔傳統產業發展可能帶來的生態破壞風險,無所作為,聽任傳統產業自生自滅。第二種是借生態文明建設之風,一哄而上,大搞生態公園等建設難度不大、景觀效應明顯的面子工程。
第一種傾向如果日趨嚴重,產業空心化現象將會蔓延,給地區乃至國家發展帶來深遠影響;第二種傾向則容易造成環保工作流于表面,對投入大、見效慢的工作望而卻步。
現在大批學者強調生態保護優先,不少地方官員也隨即奏起生態高調。但是,多數人并沒有準確理解生態優先的內涵,有的在盲目跟風。在這種大背景下,決策者更要重新審視和準確把握環境與發展的關系。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為下一階段的發展定下了基調:經濟要保證合理的運行空間;產業結構調整要進退并舉,新興產業有進有為,傳統產業重組升級,優先發展生產性服務業。
基于此,筆者認為當前環境與發展應該是共生的關系,環境保護既不是經濟增長的攔路石,也不是經濟下行的落井石,而應該成為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一塊基石。應重點把握好3個環節:
第一,制定不同地區合理的綠色GDP差別化發展指標。經濟增長指標要充分考慮各地區不同的發展方向。指標的設定要合理,要把經濟增長速度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資源環境耐受度門檻之內。
第二,充分運用環境保護的市場、科技、法律、行政等手段。把握經濟發展的綠色方向,借鑒美國“再工業化”戰略,推進以制造業為主體的實體經濟的重組升級,爭取在國際制造業新一輪布局中搶占高地。地方政府在決策時,應充分發揮市場經濟內在的活力和效率,不能簡單地“一刀切”,或放任實體經濟轉移到落后地區。相關部門要敢于啃硬骨頭,善于借助科技進步,下大力氣從制造業生產的全過程來治理污染。
第三,及時共享發展成果,經濟反哺環境,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環境治理占GDP的投入比例要能達到環境質量在較快的時間內得到改善的水平,努力做到早還舊賬、不欠新賬。
重新審視政府主管與社會共治關系
各地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現象嚴重,也導致了公眾對地方政府的不信任感日益突出。公眾參與是挽救公眾信任危機、增加政府統治和公共決策合法性的有效手段。上世紀末以來,席卷全球的新公共管理運動指明了建立一個多方參與、協調合作的新型環境公共服務體系是今后環境管理創新的方向。發達國家的環境管理轉型,就是在環境公害事件以及新公共管理運動等因素推動下一種被動的轉型,是“公眾拽著政府走”。對此,我們要重新審視政府在環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揚棄傳統的政府主管模式,認真研究各利益相關者,包括同級政府各有關部門,上下級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公民等如何建立合作伙伴關系。要讓公眾參與成為有效的社會調控機制,形成“政府與公眾并肩走”的局面。政府要主動引導,把公眾參與放在與政府和市場同等的地位來看待。要從政府一元管理,轉變為政府、社會組織、社區組織、公眾等多元共同管理。
重新審視新老環境管理制度關系
環境管理制度的不斷完善,推動著環境保護的歷程。不同歷史階段環境管理制度的重心和作用各不相同。如在本世紀初,以考核政府為主的環境保護目標責任制成為當時八項環境管理制度的龍頭。“十一五”前后,總量控制成為連接各項環境管理制度的主線。“十一五”期間,排污權交易、生態補償、綠色保險、綠色信貸等環境經濟政策相繼出臺。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這些環境經濟手段的作用將日漸明顯,勢必涉及和已有制度之間的銜接、調整,原有的制度也需要適應新的形勢進行深化、創新。
目前,以總量控制為主線的環境管理工作面臨挑戰。無論是目標責任制考核還是總量減排考核,主要落腳點均是強化政府部門的環境意識,主要通過行政手段來完成目標,雖然成效明顯,但是行政成本、社會成本過高。而且,忽視了各項管理制度之間的協調問題,也沒有徹底解決污染控制和環境質量改善兩張皮的問題。
筆者認為,應盡早確定排污許可證的主線或龍頭地位。環境管理最終落腳點是每個排污單位,協調的是其與所在環境之間的關系,最終解決的是排污單位的環境外部性問題。排污許可證是以法定的名義,規定排污單位的行為和環境的關系。而這種行為和關系,可以通過排污權交易這一市場手段,從順應企業逐利本質、順應市場機制入手,和其他環境管理制度有效結合,協同解決環境外部性問題。
因此,隨著市場經濟、法治政府、公民社會的成長,排污許可證的龍頭作用應該得到彰顯,因為其涉及總量控制、目標責任考核、環境影響評價、排污權交易、生態補償等各項制度。在推進的過程中,恰好可以梳理、銜接、整合各項制度在新形勢下應該承擔的功能,明確各項制度之間的關系,進一步提高環境管理效能。
推進體制改革要厘清幾種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