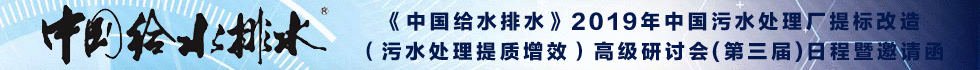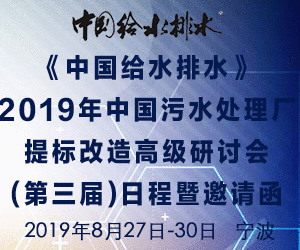從去年開始,PPP(公私合作模式)進入空前發展模式,從財政部財科所所長位子上退下來的賈康似乎更忙了,作為中國財政學會PPP專委會會長,他和他的團隊為各省PPP項目的順利推進提供技術咨詢。
在安徽首屆PPP高峰論壇現場,賈康接受了媒體專訪,對于當前的PPP正面效應及其其所關聯的混合所有制等問題,賈康認為,在城鎮化加速和地方政府背負巨額債務的雙重背景下,積極推進PPP模式將是各級地方政府在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后的必然選擇。
PPP要允許長周期談判
《中國經營報》:從去年開始,PPP在全國范圍興起,由此出現的規模大、簽約低現象也讓社會上出現了PPP上熱下冷的說法,你認為當前階段的PPP發展是否已經不理性?
賈康:不是每個PPP項目都能做成,但也不能說很多沒有做成,這是個動態的過程,現在社會上1.6萬億的投資意向還在上升,我們也能體會到企業家在商言商的考慮,一般企業會關注這個領域,但是不到一定的火候,他們也不會有實際動作。
當下的PPP不是一哄而上,需要政策給予指導,需要專業人士給出意見,篩選可能的項目,然后和政府達成一定共識以后,再進入一個個項目的實際談判中。這個過程很漫長,因此PPP項目要允許有一個比較長期的談判周期,比如說2~3年這都是一個很正常的時間周期,此前簽約的中信和汕頭合作PPP項目,前期談判就長達3年,然后才進入了實際操作階段,目前來看,我國的PPP還處于方興未艾的階段,不能簡單以簽約率來判斷是否成功,更不能簡單說就是上熱下冷。
此外,說上熱下冷也有一個積極方面,就是能夠督促政府方面做一些事情,加快政策出臺的速度,現在發改委、財政部也出臺了很多的文件、指南、管理辦法等,下一步是要在一些行業盡快建立一些試點項目,結合國際和本土的經驗及利弊得失,為大范圍推廣積累經驗。
《中國經營報》:今年以來,財政數字一直不好看,在穩增長的概念之下,PPP對積極財政政策落地有何釋放作用?
賈康:我認為應該把PPP理解為偉大的制度供給的創新。配合宏觀調控的要求,來更好地實現穩增長、調結構,這是我們值得追求的正面效應。
當然要實現這些,我們面臨的挑戰也是前所未有的,現在雖然出臺了很多的紅頭文件,但是從文件上升到法治還有一定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能坐等法律上升到成熟形式,只能以現有法規指引,積極探索和創新,一方面要積極,另一方面要審慎。
借鑒已經有的很多案例啟示,把現實需要的PPP項目,形成一個政府和非政府精誠合作的基本框架,這個大潮流我現在感覺方興未艾,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地方政府和企業家們的共識還不夠,需要從各個細節上做工作,然后形成有效對接。
符合條件的國企也是社會資本
《中國經營報》:當前對PPP的研究很多,作為研究者如何看待PPP的正面效應及其所關聯的混合所有制等機制創新?
賈康:過去我們把PPP直譯為公司合作伙伴關系,現在是指政府和社會資本。我覺得現在的意義更符合中國實際,因為中國現在風生水起的PPP中,不僅有非公的私有企業參與,還包括政府等符合條件的國有企業。
國有企業可以在符合條件的前提下積極參與各地PPP的項目建設,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主要還是在一些公共工程,公共服務、硬件支撐等有效供給項目,它的特點是把過去只有政府才能做的事情,變成政府和非政府主體一 國有企業可以在符合條件的前提下積極參與各地PPP的項目建設,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主要還是在一些公共工程,公共服務、硬件支撐等有效供給項目,它的特點是把過去只有政府才能做的事情,變成政府和非政府主體一起共贏式的合作。實現了風險共擔,利益共享。
作為政府方來說,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出政績,這是堂堂正正的決策。政府的考慮就是如何通過PPP項目,貫徹各個地方政府、決策集團以最終確定區域發展戰略。另一方面,作為企業來說,在商言商,企業要找到自己的生存發展空間。要形成和政府的合作伙伴關系,需要企業從PPP中發現投資回報,形成這種伙伴關系,還需要一些專業機構,比如律師事務所、設計師事務所、財務、會計師事務所,等機構的介入。雙方要依托這種合作關系,合在一起就是一個雙贏或多贏的局面。
因此,目前來看,PPP仍然是一個敞口的概念。在這樣一個PPP發展過程中,作為一個研究者,我認為應該把PPP看作一個制度供給的偉大創新。
PPP機制實現1+1+1大于3
《中國經營報》:在具體的正面效應上,PPP不僅是治理模式的創新,從全局看更需要地方政府發揮正面效應,你認為如何發揮其效應?
賈康:PPP的機制創新,對于政府方面來說就是要尊重市場,讓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作用,在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之下,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目前需要找一個新的機制,我認為就是PPP模式,通過和政府合作,民間資本開始在一些項目上唱主角,以民資為主的模式把建設過程變成了現實。
伴隨著中國城鎮化和老齡化的步伐,未來幾十年中國進入老齡社會的壓力很大,資料顯示,到2030~2033年,伴隨城鎮化、老齡化所需要的投入將是現在政府要面臨的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性挑戰。把城鎮化、老齡化放在一起更需要我們高度重視,只有用PPP的機制創新,政府才能更好地發揮職能。
其次,政府履職,是為人民群眾謀福利、謀利益。圍繞老百姓對幸福向往的一系列問題來看,要形成問題導向。過去政府單打獨斗動不動就超預算,兩個億能干成的事最好搞成三個億,四個億,政府效率低下,項目質量不能得到保證。有的還沒有交付使用,就已經毛病百出。有的則是竣工交付使用之后,運營和服務不能讓老百姓滿意。
對于這些問題,現在通過PPP的機制把政府之外的企業、專業機構拉進來,通過這些參與方的公建,讓老百姓滿意,提供有效供給,最終實現1+1+1大于3的機制。未來,如果我們把PPP機制更多的應用到中國更大市場上,甚至走出去,實現園區、物流中心、基礎設施項目的對接,那么就會形成我們和世界其他經濟體和平互動,一起發展。
《中國經營報》:雖然PPP機制很好,但是目前階段一些企業,特別是國企面臨著過幾年企業領導者就會換屆的問題,對未來企業總有各種擔憂,從政策上如何打消人們的顧慮?
賈康:事實上,PPP給一批企業提供了一個過去想都想不到的舞臺,我們看到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就是臺北101PPP的項目,這樣一個重要的基礎設施建設,地標式的101大廈,它和周邊的建筑合在一起已經有100年的歷史,它甚至鎖定自己家族好幾代人的前景。
從這個角度看,因為這種關系,參與方很舒心,也省心,因為他的生活質量有保障。這樣的企業加入到市場,使我們的市場資源配置更加有聲有色。101這個大廈如果是政府資源主導建設,我想估計沒人敢簽字。現在的情況是,如果沒有企業的參與,政府方面我覺得他想都想不到這樣一個辦法,也不可能把工程簽下來,所以企業的參與對項目的建設至關重要。
在政策上,四中全會最基本的要求是全面法制化,在實際生活里面,推進PPP以法治保障契約的實行是根本,但是在商言商,企業家最擔心的還是很 在政策上,四中全會最基本的要求是全面法制化,在實際生活里面,推進PPP以法治保障契約的實行是根本,但是在商言商,企業家最擔心的還是很多情況下政府方面很強勢,如果我加入進來以后出了問題,誰來保證我的權益,這一點在四中全會也有涉及。
PPP與四中全會“依法治國”“以憲行政”指導相呼應,是政府和非政府企業按照自愿原則形成一個合作契約,他們是以平等的民事主體的身份一起簽字,然后按照共同的承諾來實現契約里所保證的風險承擔,利益共享。法治環境的打造是PPP運行的一個最重要前提。
賈康:法治是PPP運行的最重要前提